通过追溯美国历史意识形态对贫困的忽视、美国长期以来对贫困的怀疑、根深蒂固且仍在持续的种族主义、反移民的态度、依赖资助流于表面的学术研究等原因,《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的作者杰夫·马德里克提请大家注意美国官方对贫困人口数据的故意低估。美国官方的贫困衡量标准是政府提供的最不负责任的统计数据之一。马德里克对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有害、最令人心碎的问题之一,美国儿童的普遍贫困,进行了根本而又不容忽视的考察。作者在本书中仔细研究了贫困儿童所遭受的伤害,并描述了这些儿童的实际生活。生活在贫困中,即使是暂时的,也不利于认知能力、情绪控制和儿童的整体健康发展。美国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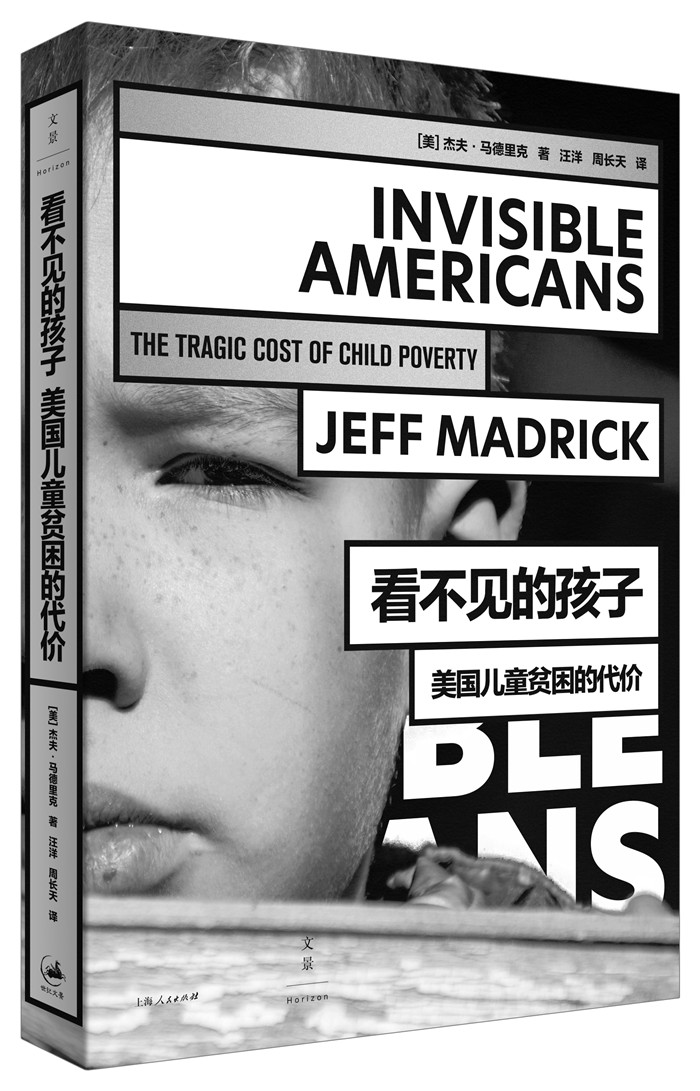
《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
[美]杰夫·马德里克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相关阅读
发生在现代的粮食匮乏
就在不久前,一群对贫困抱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在今天还有美国人吃不饱饭纯属夸张。法学家、里根总统的顾问埃德温·米斯三世(Edwin Meese Ⅲ)在1983年曾宣称他从未见过“任何权威数据显示有饥饿的儿童”生活在美国。按米斯的说法,有些人确实会去食物赈济处,“因为那里的食物是免费的,而且不用付钱多方便呀”。即便在今天,仍有人发表类似的论断。但没有人会质疑的是,缺乏足够的、有营养的食物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
美国农业部和人口调查局联合对家庭进行年度调研,了解是否所有人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联邦政府为决定合适的财政预算,已设定了两个不同的粮食安全类别。其中,“低食物安全”指仅有有限预算用于购买便宜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往往不够有营养,仅能带来饱腹感而已。而“极低食物安全”指经常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这也被视为一个处于持续性饥饿状态的指征。
生活在低食物安全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既肥胖又患有糖尿病。统计数字表明,体重偏低和儿童发育不良都与产前营养不良相关。低食物安全还可能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认知发展缓慢、生病看医生的可能性更大,以及学习表现较差等。
官方统计中的贫困儿童大约有44%就生活在低食物安全的阴影之下。这个数字在经济衰退、贫困率上升时会大幅增加。比如在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2008年到2009年,缺少食物的人变多了,但其数量随着经济“复苏”而下降了。
事实上,政府调查已经发现,即便是收入达到官方贫困线200% 的家庭,极低食物安全的发生率也要高于平均值。所以,饥饿在今日的美国并不少见。
美国孩子对于贫穷的第一印象以及最持久的体验就是饥饿。在美国,尤其在深南地区,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有人长时间吃不饱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之后的“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至少在70年代中降低了这些极端状况的可能。但时至今日,是否有东西吃仍旧是穷孩子们每一天都绕不开的问题——这也是最初让他们发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并由此产生自卑感的原因。食物的不足是最初的信号,使他们认识了捉襟见肘的生活,意识到了贫穷的存在,并因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耻。
1985年左右,赫苏斯·德·洛斯·桑托斯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爱丁堡市一个贫穷的家庭,这个地方位于美墨边境的伊达尔戈县。如今的赫苏斯已经从密歇根大学毕业,拥有社会学的硕士学位,但他走到今天的道路漫长、曲折,充满了不确定。
赫苏斯的母亲南希·洛佩斯是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后代,一辈子都在农场劳作。赫苏斯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他的父亲是个卡车司机,后来进了监狱(赫苏斯模模糊糊地记得父亲大概因为想要挣更多钱而参与贩毒了),最终离开了他们。通过林登·约翰逊总统授意拓宽覆盖面的“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赫苏斯一家人能获得现金补助,他们还能得到食品券,但仅靠这些还远不能将这个家庭的收入拉到贫困线以上。
赫苏斯一家住在一部拖车里,所有人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用电全靠从输电线上多拉出一根支线。经常有小偷打破拖车的窗户偷取他们的食物和任何稍微值点钱的东西。最终他们决定再也不锁门了。
当他们每个月的月初收到食品券后,赫苏斯的母亲会囤积很多大米、豆子之类的主食。之后他们就得开始另一轮斗争——与老鼠、蟑螂和蚂蚁的斗争。他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做煎饼想让孩子们填饱肚子,但赫苏斯清楚地记得自己一直很饿,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每天都会抱怨吃不饱,而且食品券买回来的食物总是不到月底就吃完了。
作为一个孩子,赫苏斯会因为自己家需要靠食品券以及附近的免费食物银行过活而感到羞耻,但赫苏斯回忆说,当能从食物银行拿到新鲜鸡肉、牛肉、蔬菜和水果时,他和家人是多么的期待和兴奋。当赫苏斯到了能上学的年龄之后,他开始期待甚至依赖每天在学校吃到的免费午餐,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福利项目。他的母亲在价格最低廉的折扣店给全家买衣服。而且,虽然孩提时的赫苏斯抱怨自己肚子痛、牙齿痛,但他的母亲并没有带他去看医生或者牙医,或许是因为负担不起。现在的赫苏斯牙齿仍不太好。后来他与很多家境更好、穿得也更好的孩子一起上了小学。
幸运的是,赫苏斯在学习上颇有天赋,小学校长几乎马上就把他安排在了一个尖子班里。据他自己说,他在学校成绩好有部分是因为他的母亲热爱阅读言情小说,而对阅读的喜爱会传给周围的人。赫苏斯说:“打开一本书你就能让自己开心起来。我读所有能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我们的录像机和电视机总是不断地被偷走,后来我们索性就不再买了。”
可惜赫苏斯读过的书并没能保护他免于所住街区的不良影响。从小学起,他就和“坏”孩子们混在一起。到了初中的时候,赫苏斯已经开始吸毒,还成了帮派的小喽啰。
据赫苏斯说,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有情感障碍,他本人也不能幸免,有时抑郁,有时又控制不住地狂躁。他的狐朋狗友中有些早早地进了局子,而他没成为少年犯,可算是幸运的。尽管赫苏斯头脑好用,却并没有将心思花在学习上,他的成绩很糟糕。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的母亲将他寄养到住在俄亥俄州中产阶级社区的叔叔家里。他仍旧不怎么认真读书,不过好歹是毕业了。
之后,赫苏斯当了几年厨师,过了一阵无家可归的日子,终于通过申请被得克萨斯州社区学院录取。这时候的他虚长了几岁,有了更多的社会经验,因而读书更有动力,学习也更刻苦了。他有很多科目都得到了A等,最终被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而且获得了奖学金。赫苏斯的导师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如今的赫苏斯在得州奥斯汀有了一份学习和发展引导师的工作,但或许是因为针对西裔的歧视,赫苏斯也是花费不少工夫才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并不是一个有关美国梦最终成真的故事。赫苏斯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美国人。尽管他有着不错的天赋,也踏实努力,但这些并不确保他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惶恐和不安——或许他所恐惧的是自己某一天又会变得一贫如洗。
无家可归和收容所
美国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这场危机在罗纳德·里根任期内发展得更快了,直到今天也不见减缓。2017年有33%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拖家带口的,而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家庭很可能就是下一批无家可归者。有研究曾预测全美2019年会有250万儿童失去家园,或者与家人一起住在收容所里,或者临时借住在朋友或者亲戚那儿。有些儿童甚至单独住在收容所里。他们经常需要搬家,有时甚至是连夜搬家。也有一些儿童跟着单亲家长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公寓或者旅馆之间。假如不对这场危机加以干涉,纽约的公立小学中差不多有七分之一的孩子会在小学毕业之前流落街头。仅在2015—2016学年中,纽约就有大约十万名在校儿童无家可归,其中有33000名住在收容所里。联邦政府报告指出无家可归的孩子饿肚子的可能性两倍于有家的孩子。
无家可归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一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开。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无家可归的儿童健康水平更差,认知发展延迟,且毕业率更低。
劳伦是曼哈顿下东区一家小学的心理治疗老师。她特别关注遭到虐待或者生活条件特别差的学生。她帮助的很多孩子都住在收容所里。马克(化名)是所有孩子中她最担心的一个。据劳伦说,马克的母亲好像酗酒。儿童服务保护中心已经好几次因为马克的妈妈对他漠不关心而将他带走。当马克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或者是跟着她去某一个收容所,或者住在她朋友的家里。而且马克的妈妈经常夜不归宿。
劳伦说:“对马克来说,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一天。他经常非常饿,很疲惫,明显没精神,很情绪化。”马克在学校的表现也很差,而且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他已经11 岁了,但仍在上三年级,已经留级两次了。
布里安娜现在是个收入不错的社工,但她和她丈夫曾经一度流浪街头。有一段时间,他们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汽车旅馆里,后来住在收容所里。救助机构经常按不同的性别安排睡觉的地方,因而一家人往往会在收容所里被拆开。布里安娜待的收容所不允许她为自己有严重哮喘的儿子携带药物,于是小男孩只能跟着爸爸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里。
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的白人社区,尤其是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是美国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地方,几乎达到50%。在田纳西州的莱克县,有46% 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汉考克县是42%。这些地方的收容所也与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时好时坏,而且对住在里面的人约束颇严。
即便在有着相对发达的福利制度的大城市里,埃丁和谢弗描写过那里的收容所:“有些只接受女性,而且带着的孩子不能超过5岁。有些会要求入住的人参与宗教仪式。有些只接受刚刚失去住房的人。而还有一些会强制进行犯罪背景调查。有些收容所有很不错的网站,而有些则根本没有在网上更新过信息。有时候你只能打电话进行咨询,还有一些收容所甚至只靠人们口口相传。因而,要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或许会花上好几天时间。假设你终于找到一个自己符合要求可以去的收容所了,而且那里也确实还有空房间,你或许会发现自己得拖着所有的行李长途跋涉,穿过整座城市才能抵达那个地方——当你没有钱的时候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现行福利体制的失败:最有需要的人却得不到帮助
致使贫困率无法下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新实施的TANF与被其取而代之的“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FDC)相比,现金补助的力度大幅下降。如今的TANF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不但能够从中获得的补助额度大幅缩水,受惠者还必须满足工作要求,所以根本无法帮助家庭摆脱贫困。事实上,很多被迫工作的人仍旧很穷。
经济学家罗伯特·A. 莫菲特认为:“一方面,AFDC 项目被TANF 取代造成补助覆盖范围大幅缩水,意味着在1983年有57%的私人收入属于赤贫状态的单亲妈妈家庭能够领取福利补助,但到2004 年就只剩下20%还能领得到了。”社会福利支出不再把钱留给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孩子,而是更多地分配给了有工作的已婚夫妇以及老人。
莫菲特还说:“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由于EITC项目的覆盖面大幅扩大,有工作且年收入达到大约10000美元的单亲妈妈家庭从中获得了可观的额外补贴。后来开始实行的CTC也为有工作的单亲妈妈家庭提供了更多补助,不过对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则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用。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福利待遇的重新分配,最贫穷的单亲妈妈家庭原本能拿到的福利被分给了更高收入的家庭。”
自莫菲特发表这篇文章之后,CTC每年的补助额度上调到了2000美元。但他的主要观点仍旧成立。算上包括社会保险、医疗补助等穷人也能受惠的福利项目,莫菲特估计美国所有社会福利开支中有六成都发给了那些实际挣得的收入高过贫困线200%的人群。
总的来说,如今美国的社会福利项目与我们想象的已经完全不同了。严格的工作要求以及领取TANF有时间限制——最长五年——已经让很多原本的受惠者望而却步。积极寻找工作的要求劝退了很多申请人,因为找工作不仅有经济成本,更耗时间。2015年,TANF的开销只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0.5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反对现金福利运动就非常具有效果。2015年领取TANF补助的家庭只占所有贫困家庭的23%,在TANF刚刚开始实行的1996年,这个数字是68%。在14个州里,只有10%甚至更低比例的家庭领取TANF补助。而能领取的福利即便是已经就通货膨胀有所调整,仍旧远低于1996年当TANF计划刚刚通过时能够领取的额度。而原本福利项目的补助额度,即大部分州的AFDC补助额度,也在1970年到1996年间下降了40%。
目前的TANF项目由各个州自行管理,在所有提供这一社会福利的州中,补助上限都是不超过官方贫困线的60%。有34个州规定福利待遇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30%,而有18个州甚至不到20%。各个州还有各种办法让穷人们无法享受TANF福利。比如,2016年,在密西西比州,每月的福利待遇最高仅为160美元。在相对慷慨的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取的福利待遇为715美元,但那也不过相当于当地贫困线的大约40%。此外,所有据说满足工作要求就能获得的福利中,EITC在促进女性就业方面更有作用,通过税收抵免而提高的收入就像胡萝卜,而TANF的工作要求就是大棒了,胡萝卜胜出。平均来说,一个符合标准的三口之家每月能够通过TANF领到447美元补助,但在14个州,三口之家每月能够领到的补助不足300美元。
对于那些无法就业的人而言,美国是个分外残酷的地方,他们的孩子也不得不跟着他们受苦。将SNAP和TANF福利加在一起就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父母们唯一的经常性收入了,这样一来,就只有在一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家庭预算仍能达到官方贫困线的75%。在大约20个州,两个福利项目的补助加在一起差不多等于贫困线的50%或更低一些,在还有20个州,补助也不超过贫困线的60%。
对于贫穷起因的意识形态之战并不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真实的后果会发生在穷人身上,会影响政策的推行或终止,会对美国人对于谁应为贫困负责而产生影响。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了美国媒体对贫困状况以及贫困与社会政策之间关系的报道,结论是确凿的:美国人“对穷人抱有一种负面的观点”。与之相反的是,在欧洲进行的调研则显示欧洲人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制度化问题,而非抱持着个人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观点。在多个可能导致贫困的原因中,有70.1%参与调研的法国人选择了“社会不公”。有87.9%参与调研的克罗地亚人也选择了这条原因。
“二战”后的美国除了这些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当然也少不了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我甚至可以说,种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福利制度改革的核心,种族主义也是这个国家无法将贫困率降到合理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
作者:[美]杰夫·马德里克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