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蓝》
[美] 莱斯莉·贾米森 著
高语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纽约时报》推荐作家莱斯莉·贾米森继《十一种心碎》《在威士忌和墨水的洋流》之后的非虚构新作。14个相互独立的故事,聚焦于一个直击灵魂的共同主题:比海更深的渴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沉迷。她向这份渴望的本质发问,并尝试做出最为真挚的回答。她满怀包容的深情讲述,映照了人性之复杂,之幽微,之动人。

精彩文摘:
我们跟自己讲故事,为的是再活一遍
2000年4月,路易斯安那一个名叫詹姆斯·莱宁格尔的幼童开始做一些有关飞机失事的噩梦。每当他的母亲来到他的卧室里安慰他时,都发现他的身体扭曲着,手脚使劲摆动踢打,仿佛正挣扎着想要挣脱什么。他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话:“飞机失事!飞机着火!小朋友出不去!”
在之后的那几年里,这些噩梦的故事情节变得越来越清晰。詹姆斯最终告诉他的父母,这些是前世的回忆。他说自己曾经是一名飞行员,他的飞机被日军击中坠毁。他开始用到一些专有名词,令他的父母十分不解。他所驾驶的是一架“海盗式飞机”。他从一艘名为“纳托马湾”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他的父母从未跟他谈及过二战,也无法想象他怎么会出现这些幻觉。詹姆斯跟他们讲起了他在舰上的朋友们:有个名叫杰克·拉森的人,还有沃尔特、比利和莱昂,他们都在天堂等着他。他用这些人的名字命名了他的玩具特种部队成员。他的母亲安德烈娅开始确信詹姆斯在回想前世,父亲布鲁斯则半信半疑。
然而,当布鲁斯着手研究时,便发现有些信息让他难以再持怀疑态度。1945年,有一艘名叫“纳托马湾”的航空母舰曾被派往硫磺岛,船员包括杰克·拉森和詹姆斯·休斯顿两位飞行员,而他们就在那一年3月3日在父岛附近被击落。纳托马湾号的船员还包括沃尔特·德夫林、比利·皮勒和莱昂·康纳,所有人都在休斯顿丧生之前牺牲。一个小男孩怎么会知道这些人?更别提他们这艘舰的名字和他们死的顺序了。
2002年,布鲁斯参加了一场纳托马湾号船员聚会,并开始问问题。他并不准备告诉大家他的儿子所回忆起的内容,他告诉所有人他正在写一本有关这艘航空母舰历史的书。安德烈娅则对军史不感兴趣,她只想让儿子结束梦魇。她告诉詹姆斯,她相信他说的话,但是前世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要过好今生今世。
为了让詹姆斯彻底释怀,在他8岁的时候,一家人来到了日本。他们计划为詹姆斯·休斯顿举行一场悼念仪式。他们搭了15小时的渡轮,从东京来到父岛,又乘一艘小船来到休斯顿的飞机坠毁的大致地点。就在那里,詹姆斯向海里扔了一束紫色的花。“我向你致敬,永不忘怀。”他说。然后,他抱着母亲的大腿啜泣了足足20分钟。“你就在这里把一切都放下吧,伙计,”他的父亲告诉他,“就在这里把一切都放下吧。”
当詹姆斯最终抬起头并拭去眼泪时,他想要知道他的花去了哪里。有人指向水面上遥远的一点紫色:它们就在那儿,遥远但依然可见,依然在漂,在海面上越漂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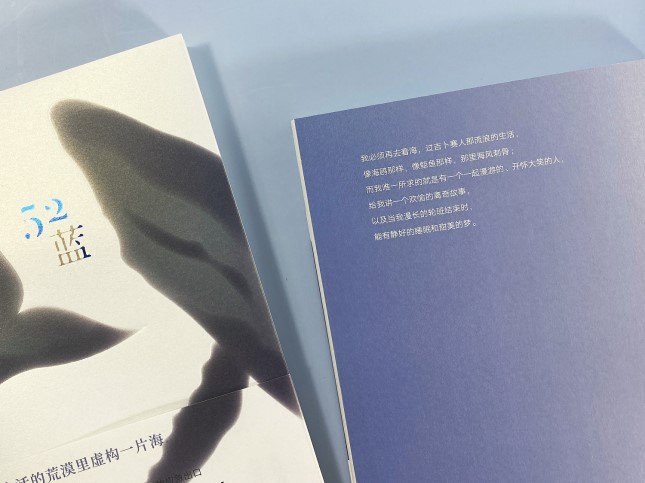
2014年1月晴朗的一天,我来到弗吉尼亚一家名为 DOPS(感知研究部)的研究所,访问一位名叫吉姆·塔克的儿童精神病医生。他花了14年的时间汇编了一个数据库,收集号称记得前世的孩子的资料。我见到塔克时,他的数据库已涵盖了逾 2000个家庭。不过,他把詹姆斯·莱宁格尔列为最厉害的案例。
我当时是受纽约一本时尚杂志之托采访塔克,而且我明白杂志的编辑期待我写出一篇驳斥性的文章。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在写一篇关于DOPS的文章,而该研究所主要研究前世回忆、濒死体验和超感官知觉时,别人就会说:“等等,你说啥?”它轻易就能惹来别人的嘲笑。然而,从一开始,我就有为轮回转世之说辩护之心。倒不是说我坚信它,而是说我已对怀疑论本身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似乎对人、对方案、对信念体系鸡蛋里挑骨头,要比建立、捍卫或至少是认真对待它们容易得多。那种预设好的不屑一顾抹杀了太多神秘和惊奇。
转世之说本身并不稀奇。我们都思忖过自己死后会如何。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33% 的美国人相信有轮回转世,而2013年的一份调查问卷则估算有64%的人相信定义更宽泛的“死后灵魂不灭”。在我居住的纽约,坐地铁时我总看见在10月走失的一个13岁自闭症男孩的照片。那个孩子住在皇后区,没有哪一辆经过皇后区的列车上没有他脸部照片的。我不理性地确信,他们会找到他,或者,不论在哪里,他都会以某种方式,安全地活着——如果那样相信让我显得愚蠢,那么我宁可做个傻瓜。
DOPS的办公室位于夏洛茨维尔市中心一座雄伟的砖楼里。塔克来欢迎我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怪人或是神秘主义者。他风度翩翩、头脑清晰,显然是个聪明人——人到中年,正在脱发,但轻盈而瘦削,就像是你高中好友那个跑马拉松的爸爸。他镇定自若,带着一丝彬彬有礼的客套。他说话很小心,却无可置辩,解释着某些媒质如何招来死者的魂灵,而胎记则可以证实前世受的伤。那有点像是在听研究酸的地质学家就事论事地描述土地的构成。
DOPS成立于1967年,严格来说是隶属于弗吉尼亚大学的,但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私人捐款。 在塔克带我参观那些办公室时,我在笔记本里潦草地记下了一系列奇怪的细节,都是这个地方让人轻易可以发现的与众不同之处。公告栏上贴满了写着励志言辞的纸张(“我们对于头脑和物质的认知必须经过多个尚无法想象的阶段”)和描述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的传单(“对于声称可以提供死者信息的媒质的研究”“癫痫的超凡经历”)。我们走过了“加护室”,它是为超感官知觉实验而设计的:一个看似阴森的洞穴,里面有一张活动躺椅,参加实验的人坐在上面等待接收“发信者”从大楼另外一个地点发出的信息。塔克解释说,这间房间的设计是后来才完善的——墙壁上都覆盖了金属薄片,以防止用手机作弊——似乎默认我可能已经知道超感官知觉实验室的构造了。

DOPS图书馆里有一只巨大的玻璃箱,里面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武器——尼日利亚短剑、泰国匕首、斯里兰卡剑——它们对应着据说会转世的伤痛。一把缅甸大头槌下面的标牌上写着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僧侣遭精神错乱的访客击中头部,据称在几年后转世投胎,成了一个头颅骨异常扁平的男孩。在附近的一条走道里,放着一堆堆介绍各种DOPS研究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的标题是“与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有关的另外七段超自然经历”。我们走过一面墙,有两把勺子被固定在墙上,其中一把是弯的,仿佛它曾被扔进火里熔化。当我向塔克问及这两把勺子时,他的回答很是若无其事。“那些么?”他说,“弯曲勺子实验。”
还有就是那把锁了。DOPS的首任所长伊恩·史蒂文森在2007年去世时留下了一把锁,锁的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想,如果他的灵魂可以超生,就会想办法回来,揭晓密码。塔克和他的同事接到过好几个电话,建议他们尝试某些密码,但至今都没能把锁打开。在跟我谈及这把锁时,塔克的声音里终于流露出一丝揶揄的淘气。不过,在我们参观的过程中,他对于讲转世投胎的笑话表现得非常节制。当晚晚餐时,他告诉我他曾经尝试写小说,但当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再次写作时,他却笑了。“或许来生吧。”
塔克告诉我,一边当持证执业的儿童精神病医生,一边在DOPS任职,让他颇觉自我分裂。他简单介绍了数据库的构成:他的大部分案例都是2到7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回忆。这些回忆以生动丰富的梦为主,并充斥着各种情绪——恐惧、爱、悲伤。大部分孩子都来自外国,有许多孩子是塔克尚未谋面的。不过,当有新的家庭找上门来时,他会定期对他们进行访谈。当似乎可信的前世身份得到辨认(通常是家族中的某个人),他便会将其列为“已解决”案例。不过,也有个别像詹姆斯这样的案例,其前世是个陌生人。
数周之后,当我聆听我们访谈的录音时,我很尴尬地听到自己不断地向塔克宣称自己“对神秘事物抱有开放心态”。我那么说是认真的,但我也能听到自己声音当中刺耳的自我说服、过分积极的语调,还有策略上的精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在试图说服塔克我并不是另一个怀疑论者。
在我拜访塔克时,我已经参加十二步骤戒酒复原计划3年多了。 我发现,要实现这种复原必须同时彻底放下(至少是暂时放下)许多怀疑:对于教条,对于陈词滥调,对于有洞见的计划和预先伪造的自我意识,对于其他人对自我人生看似刻板的、表面的描述。在复原过程中,我们被要求避免“在调查之前就予以藐视”,而写一篇有关转世投胎的文章——参观DOPS及其弯曲的勺子——就像是另一种测试,看我是不是愿意保持开放心态。

写作多年,我一直很喜欢琼·狄迪恩的散文《白色专辑》。这篇文章的开头很出名:“我们跟自己讲故事,就是为了活下去。”它的结尾不那么出名,不过几乎是同一个意思——狄迪恩重申了她对于所有这些“故事”及其虚假的连贯性的怀疑,仿佛她还没将这一观点反复强调好几遍似的。最终,我开始对她的怀疑产生怀疑。我讨厌其沾沾自喜——她如何在一个充满自欺的世界里,将自己说成看破一切的怀疑论者。我开始相信,怀疑论本身就带着伦理上的失败,那就像是在复原会议上拒绝陈词滥调,或是完全驳斥他人对自己人生过于简洁的陈述的冲动背后的势利。
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越来越痴迷于描写一些或许在他人看来很可笑的人生和信仰:有人声称患了一种大多数医生都不相信它存在的皮肤病,有人自称与世隔绝却跟一条难以捉摸的鲸鱼产生了精神共鸣。然而,坦白地说,这种偏爱也带有一抹自以为是。或许我喜欢告诉自己,我在为弱者辩护。又或许那是怯懦。或许我太害怕了,对于人们为了继续活下去而跟自己讲的故事,没有办法予以拒绝。
这次,倒不是说我被塔克有关投胎转世、貌似“围绕物理学”的解释完全说服了:这套理论基于从物理学历史中选取的一系列实验,而我采访的一位物理学家说这些实验是“精心筛选过的”,并且被选择性地予以错误阐释。无论如何,塔克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而不是一个物理学家。重要的是,我在情感上、精神上和理智上都排斥某种表示自己知道得更多,知道何为可能、何为不可能的轻蔑语气。假设我对意识本身——它是什么、来自哪里,还有,一旦我们用不着它了,它又去向何处——有多么深的理解,似乎是一种傲慢。
在弗吉尼亚,我陪同塔克对两个家庭进行了访谈。两个家庭中都有从小就记得前世的青少年。
我的回程航班因为弗吉尼亚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而被取消了,我便在机场附近的一家行政酒店住了两晚,在大堂酒吧里一杯接一杯地喝气泡水打发时间。随着电视里不断播报各种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新闻,酒吧侍者和我痛苦地四目相对:腐败、性骚扰、死去的海豚血染日本一秘密海湾的海水。在我心灵深处某个未被提及的部分,我已经说服自己,不可知论和忍受本身是美德,但实际上,我并不确定。假装我的信仰体系足够宽容,视一切同等合理,这或许并没有帮到任何人。或许有些经历是我无法理解的,有些事情是我无法相信的。
既然如此,我到底为何要为这些前世故事辩护呢?倒不是说我想要证明投胎转世是真的,而是我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故事会吸引人们去相信。如果我们跟自己讲故事,为的是活下去,那么从让我们再活一遍的故事中,我们又得到了什么?那不止是缓和了死亡的可怕终局,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受到无形的或无法理解的力量的影响。
暴风雪还在继续,就在快要上床睡觉时,我在机场酒店酒吧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亚冯特·奥肯多,那个走失的皇后区男孩。他的尸体被从东河里打捞上来。当警方以为还可以找到活着的他时,他们放过一段他母亲录制的录音,以便帮助他信任他们:“亚冯特。我是你的母亲。你是安全的。向着灯光的方向走。”
(本文摘选自《52蓝》,有删节)
作者:莱斯莉·贾米森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