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地理概念作书名,其实反而富有文艺气质,譬如亨利·米勒颇富争议的《北回归线》,尽管小说里并没有明确提及这条重要的纬线。当然,陈福民新作《北纬四十度》定位非虚构,正是围绕这条纬线而来。北纬四十度,在中华版图上,大略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也是两种文明的过渡带,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线上,充满争竞折冲博弈融合,而绵延的长城宛若游龙颉颃其间,成为其间最具辨识性的地标。
上述两种文明,本书更习惯表述为游牧文明与中原定居文明。有意味的是,作者发现,如北魏拓跋氏、北齐高氏那样成功进入北纬四十度以南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在对接和习惯中原文明的同时,立刻就要面临这条经典纬线的传统压力,也即北部边境的安全和稳固问题——除非像清帝国那样“把防卫线向北推进到了‘无限远’”。
就历史题材写作者而言,从某一个时间点入手,可以展示限定时间段内各色人物及事件于空间切换下的不同动态,譬如曾经影响本土学术写作形态的《万历十五年》;而从某一个地理位置譬如本书选定的这条“中原定居文明的生命线”入手,则可以在历时的纵轴线上呈现不同时间切片下各色人物及事件的诸般生态——陈福民称之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这是说来寻常实际蕴含智慧的写法,当然也是相当不方便讨巧的写法,需要耗费太多力气和时间做足功课。
所谓功课,一是近乎穷尽地阅读相关文献,再则是认真踏实的实地考察。这两点陈福民都做到了。前者当然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及相关著述中披沙拣金积蓄素材,而后者则需不辞辛苦周折奔波亲身体味。一句“写到的所有主体地点,我都实地考察过”(页470),实在不是浮躁时代的人轻易能够并且肯于付出的。
非虚构的历史散文也许不必过于追求小说模样的生动,但却需要设身处地的现场感。即便是历史尘烟掠过千百年之后,拂去年代层的堆累,现场感依然可以再现,重拾某些历史的细节,从而廓清诸多“纸面地理学”的弊端。譬如书中提到,“土木之变”英宗回京路线由西向东的顺序是宣化、土木,然后希望进入土木东边的怀来城。但是现代地图标志怀来县却在土木西边。史载无误,地图也没错,只是明代的怀来城,后来在修建官厅水库时被淹没了,现在的怀来城是另选新址重建的;而现在地图上显示的“土木之变遗址”也并非事发原地,而在其南五里左右的老营洼村:这些都是实地勘察才能获得确认的。当年太史公正是有“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的亲历,方才能“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应该是陈福民勉力效法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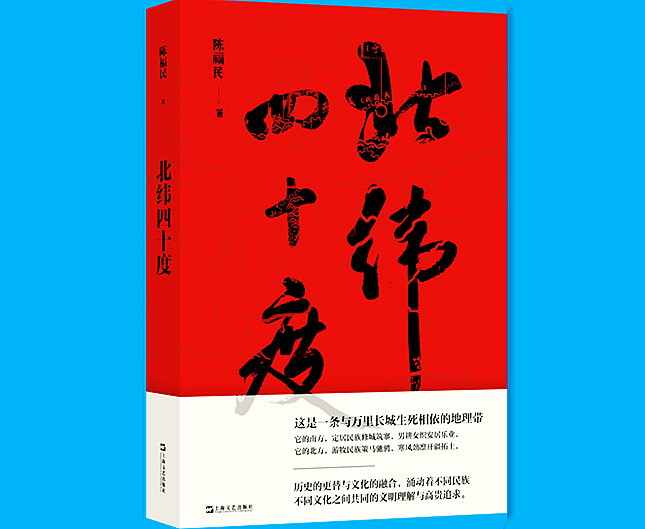
▲《北纬四十度》,陈福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福民说,自己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实在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叙写,不论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还是非历史专业的“跨界”者,其实都非易事。陈福民秉持“如履薄冰”的写史心态,依托踏实认真的功课,下笔自有从容底气,文学出身也为他的叙述带来富有可读的故事性,方便于驾轻就熟间娓娓释放文采,时时闪现的深切史识也惯常以金句呈现:“文明本身具有一种将悲剧转为喜剧的能力,维持一个彼此安全得利的短暂局面,将那毁灭的真相隐藏起来,并且努力向后延宕,等着下次的纷争再度出现”;“历史也并非总按照牌理出牌,它总是有着非常难以捉摸的魅力”;“一旦看不清历史真实,总以为牺牲是别人的事情,是天神下凡拯救地球,那很容易在自己必须有所牺牲时就去哭倒长城”——这些都在在说明,他完成了他的努力。
陈福民自言,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限于个人目力所及,我关注到《北纬四十度》,始于安禄山唐明皇这对君臣纠葛的《渔阳鼙鼓何处来》,而我个人则对前四史时段内的诸篇更有兴趣,譬如,被陈福民以虽败犹荣类比于罗伯特·李的李广、武帝时期汉匈战史上声名卓著的卫青霍去病舅甥,以及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等。
陈福民注意到,“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完成的。”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或许更自洽于娱乐立身的选择性消费,至于真相如何,未必在他们的享受半径之内。某种意义上,《北纬四十度》在许多地方,校正了以往被文艺尤其是俗文艺带偏的视听。
譬如,王昭君的出塞故事,即便所谓的读书人,也未必真的注意到,这一回的和亲背景,远非大众印象的格局。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与冒顿单于开启和亲,有文景之治声望的两代皇帝,对匈奴要人要财而仍不时掳掠,只能听任;而汉武帝时则彻底改变了彼我态势,在卫青霍去病这对“专为北纬40度而生的军事天才”的强大攻势下,匈奴直线走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到呼韩邪单于登位时,已然是“强弱有时,今汉方盛”,只有“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才可以“匈奴乃定”。而其兄郅支单于被陈汤斩于康居后,终于促使呼韩邪“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民族和解格局之下的和亲其实于汉匈双方都是有益的,结束双方杀伐恩怨,缔造河清海晏万方乐业,于是元帝“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这些史实固然班班明载于史籍,然在不断层累的民间讲述中则是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毛延寿的故事和昭君的颜值才是大众的兴趣所在,“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陈福民此言可谓犀利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全书末篇《遥想右北平》,从写法到情绪都与其他篇略有不同,有点卒章言志的意味,不妨视为陈福民对家乡的致敬礼赞:“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它是我亲爱的故乡,是我的精神乐土。”
我曾不揣冒昧问他,对北纬四十度的关注,是否和家乡有关。他的回答是:我不能在“科学”意义上确定,但就个人感受说,肯定有关系!我以为这是一个情结,而他则借张承志的话而归为“定数”。
作者:半 夏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