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老子是一家吗?为什么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怎样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何谓天?何谓人?”什么是真正的逍遥,又该如何对待生死?
《庄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出色的文字、精彩的寓言故事,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思想,真正参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塑造。陈引驰教授是《庄子》乃至道教佛教文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自2002年开设“《庄子》精读”课程,迄今已近20年,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打通前后章节,真正理解《庄子》内涵,解析精到,深入浅出。此次出版的《庄子讲义》,以原授课讲义为基础,结合其多年钻研心得及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梳理条块,自“道家老庄思想通说”至“庄子其人其书”,再至逐章讲解,更补充“《庄子》之后的思想波澜”,形成通贯的格局,陈引驰教授有关《庄子》的精妙见解尽汇于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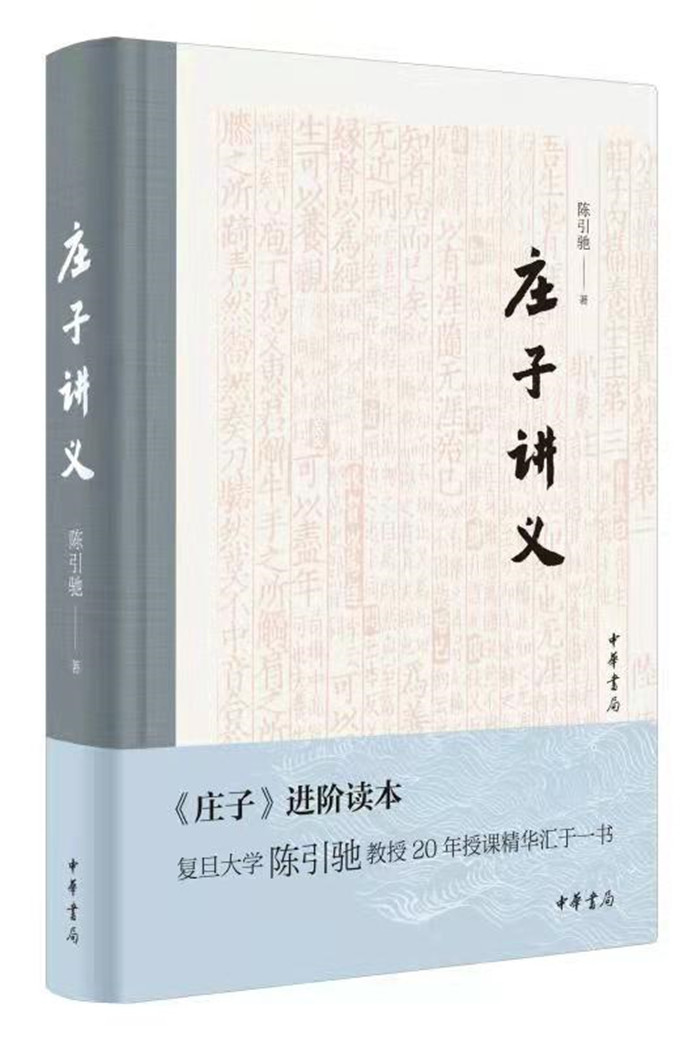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庖丁解牛”属于《庄子》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之一。这当然首先因为它非常生动。“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庖丁解牛时的全身动作形容得非常具体而形象。“砉然”“响然”“然”,则刻画解牛时的种种听觉印象,尤其“奏刀”,将挥舞解牛刀的动作和声音合而为一,且领起下文“桑林”“经首”的音乐比喻,紧凑而无赘言,显示了很高的文字表现力。
《庄子》中有许多涉及技艺的寓言故事,都很生动,而且深得其中的奥妙,“庖丁解牛”自不例外,庖丁对答文惠君的一番话便极为精辟。“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从主观方面清晰区分了解牛技艺逐步纯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见无非全牛”,这还是初步的阶段,在解牛的庖丁眼中,牛还是一个庞然大物,有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第二阶段是“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这是说眼光不再犹疑,而专注于所欲下刀的具体部分,“熟于筋骸之会,知其何处可断,虽属全牛,但见其支节分解”,也就是透过表面而深得解牛之关键了。
这两个阶段的差别,成玄英《庄子疏》借修道以阐明:“初学养生,未照真境,是以触途皆碍”,“服道日久,智照渐明,所见尘境,无非虚幻”。见得“尘境”“无非虚幻”,也就是窥知真谛了。
习艺过程中这种熟而生巧、专心致志的状态,《庄子》有深刻的领会,《达生》篇: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蹶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痀偻者”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一方面熟能生巧,一方面“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达到“承蜩犹掇之”的境界。后一方面,痀偻者自己形容说是“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也就是他的精神完全聚集在蜩翼上,此外所有的天地万物都不在其关注视野之中,这不正类似于庖丁之“未尝见全牛”吗?“方今之时”是第三个阶段,“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成玄英《疏》曰:“既而神遇,不用目视,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废,从心所欲,顺理而行。”这时,外在客体的种种都不构成限制而不必萦心了,也可以说达到了完全自如自由的境地。
这最后的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其实并非绝对自我的,而是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个“规矩”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主体对之了然于心,甚且与之冥合为一,它也就似乎不构成限制了。这从文中“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可以得到印证。“天理”“固然”,在庖丁解牛的具体境况里面说,就是牛的本来天生的肌理、骨架,所谓“大郤”“大窾”“技经肯綮”之类。如果能够依照这些肌理、骨架“奏刀”,则不会有“横截”“妄加”的情况,“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刀自然可以“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如果说寓言是“藉外论之”,那么,庖丁解牛的故事只是所“藉”之“外”而已,并非本旨;本旨是“养生”要义。庖丁自谓解牛有更高于“技”的“道”,透露出解牛技艺中包含着更深的意味;文惠君“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更表明解牛的经验、心得可以横通于养生。论其要点,即在“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则“游刃有余”数语,陈碧虚的理解大体是恰当的:“解牛者,观其空隙之处,游刃舞蹈,以全妙技;养生者,岂不能避患深隐,保形不亏,以全天真乎?”趋避祸害,游走在种种限制和障碍之间,走出一条保守形神不亏的道路,这和庖丁解牛之道,是相同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天理”“固然”就具有超越牛之肌理、骨架的具体所指之上的意义,它指向天道自然。在《山木》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清楚表达: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人们对此节的深刻印象往往在所谓“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以树为喻,《庄子》中屡屡可见,多强调不材得尽天年,如《人间世》的“匠石之齐”与“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两节即是。然而单纯强调“不材”似有偏颇,只是从特定的角度展开的论说。《山木》篇的这一节文字,在“材”与“不材”之间做了辩证,如同《人间世》“不材”的根本意义在可以保全自己、尽其天年,《山木》篇或“材”或“不材”也是为了保全自我,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在不同处境下的不同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材与不材之间”并非《庄子》的根本抉择,文中明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真正从根本上保全自我的路径是“乘道德而浮游”,“浮游乎万物之祖”,也就是与天道自然同其浮沉,融合为一。显然,《山木》此节的意思,与《养生主》“缘督以为经”的行于中道、“循虚而行”之义,确可相互沟通。
——摘自《庄子讲义》,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陈引驰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