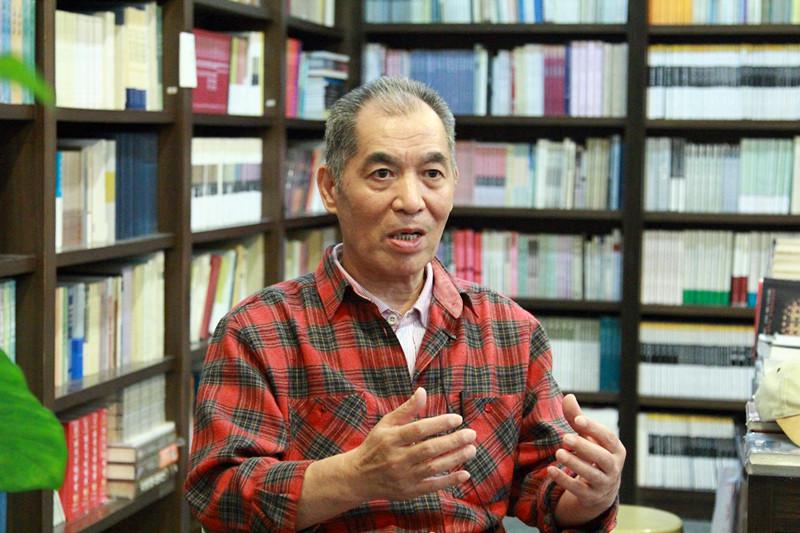
所谓喀戎,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人马”。它们分为——一类是人类的朋友,好莱坞电影中多次出现过;一类是人类的天敌,危害人类没商量,有时完全是出于任性,突发暴怒,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任何原因。不但危害人类,也攻击神族。故宙斯曾告诫诸神:“勿招惹彼们,那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曾偶然从画册上见到一幅“人马”的雕塑图片,是罗丹的作品。那“人马”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上身即是人的那部分,向上伸直双臂,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不达目的不罢休地,竭尽全力想要从马也就是兽的下身中脱离出来……
近十几年,每当我叩问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时,总是会联想到罗丹的“人马”。
人类无疑进化了的;不靠文化仅靠科技不能实现进化。往三四百年以前的历史回望过去,结果会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人类才是人类恐怖的天敌;人类对人类的凶残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凶残。任何其他物种都不会仅仅为了取乐而折磨其它物种,更不会自相虐杀、娱乐;人类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乐此不疲。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进化了。
但进化了的人类也就是“成功”地从人马的“下躯”之中脱离出来能以双足站立了的人类,心性就绝不再受“人马”之基因的影响了吗?
有些人做到了。他们可谓是“大写”的人,“纯粹”的人。
有些人仍在向往,所谓“进化尚未成功,自家仍须努力”。
有些人并无再进化的愿望,本质上还是“人马”,并且自适着。但人类的社会毕竟已经特别文明,治理社会的能力一再提高。所以本质上还是“人马”的人渐成少数,且不敢任性地造次了。这是人类进化的成就,使少数“人马”也具有了“后人马”的策略——寻常看不出,偶尔露凶暴。
而我以己眼扫瞄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所见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
我不属于第一类作家。但我也创作过第一类作品,如《恐惧》。正因也创作过,深觉那不能成为己任,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我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我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是未得要领。
于是,我的创作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于是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
这样的人是大多数。继续进化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命本能。这种本能的过程非是花蕾开放般的过程,而是自己对抗自己,自我挣扎的痛苦过程;失去的是马蹄和马皮,获得的是人的“全身”。
伪装的马蹄和马皮对于人也依然是有失尊严的;并且伪装而久也属疲劳之事。有痛苦则有深刻。我试图从此种痛苦中窥见深刻。
我之欣慰在于,古今中外,与我抱持同样之文学理念的作家居然不少,作品也比比皆是。我只不过在重复地做他们做过的事。我不因此而羞耻。

重复有重复的意义——为那些正努力从马腹中挣脱出来的人和自己点赞,在我这儿是为意义也。最后,当然也得说说我的新作《我和我的命》——只字不说就等于没完成约稿任务啊!
新作中的人物,如文婉之、李娟、张家贵等,几乎各自都有干脆像“后人马”那么自适地活在人世间的理由,但各自都不甘于那么活着;各自都认为那么活着也活得太没“人样”了。
方婉之们不怕“平凡”地活着,而怕自己会自适于像“后人马”那么活着!我以新作向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同胞致敬!倘他们非是虚构的人物,并且存在于我的“社会关系之和”,我会引以为荣的,也会使我更热爱生活。
在我看来,倒是某些似乎“了不起”得很,“不平凡”得头快触到天了的人,其实本质上只不过是“后人马”,伪装成麒麟皮的马皮之下,包裹的是违背进化论的魂。
小说中,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生活依然复杂性,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我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更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同时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
李敬泽说过,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我愿意迎难而上,保持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
对金钱和财富的无止境的贪占心是可耻的;倒是方婉之和李娟们那种平凡而有尊严地生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有着成为优秀“新人”的潜质——起码相对于各自的上一代人是“新人”。
向方婉之学习!
向李娟致敬!
作者:梁晓声(知名作家)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