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简称“中央文库”)遗址位于上海市西康路560弄15号
这里是1935年2月至1936年下半年“中央文库”所在地。1932年下半年,中央委派陈为人负责管理中央文库,其妻韩慧英等协助管理。“中央文库”集中收藏着中共成立后10余年的大批文件资料。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陈为人与妻子装成富商家庭,将文件保存在家中。1935年2月,韩慧英在外出接头时被特务逮捕。为了确保“中央文库”安全,陈为人立即搬家,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高价租下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白色恐怖下,管理者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能艰苦地独立支撑。
1936年下半年,陈为人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将“中央文库”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移交给其他同志后,于1937年3月13日因劳累过度病逝。
后来,“中央文库”几经转移,管理也数易其人。上海解放后,由陈来生同志将104包(16箱)15000余件文件完好无损地交给上海市委,后移送中央档案馆保存。
“中央文库”旧址已被拆,现为联谊西康大厦。
(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面对蒋介石高高举起的屠刀,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南昌城头,从井冈山麓出发,万水千山,前赴后继,奔延安,进华中,入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千万公里地运动作战,最后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伟岸身影投下的一个影子,一支神奇的小分队,容纳着核心机密的特殊战队——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简称“中央文库”,在敌人严酷统治下的大上海,在中共重要机关屡次遭遇重大破坏的恐怖岁月,两万余件绝密材料,屡次搬迁,惊险地躲过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艰难但安然无恙地坚持了二十几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这批记录着中共由幼小走向壮大的珍贵资料,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档,反复在旧上海嘈杂的街头跋涉,单就物理距离而言,其历程长短,当然与人民军队征战的路途不可相比,但是,其间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千钧一发之际爆发的智慧与胆量,让研读往事的后来者,敬畏而泪流不 已。
(二)
为了对“中央文库”经历的风险,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先简略介绍一下,两万余件、分装成二十多箱的珍贵文档,在反动势力铁笼般统治的上海滩,二十几年中艰险跋涉通过的主要路 径。
1926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接近尾声,上海处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交锋的第一线,当国民党即将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之际,依照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意见,为保护党的历史和秘密,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于上海戈登路(现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建 立。
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重要机关危机重重,二十余箱文件,紧急搬运至法租界恺自迩路(现金陵中路)一幢独立小楼,这是管理者张唯一的 家。
1932年,因为管理人改成陈为人、韩慧英夫妇,“中央文库”搬迁至陈家明月坊三层的独立小楼。其后迫于环境恶化,屡次搬迁,曾搬往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一位白俄的楼上。
1935年2月,“中央文库”的单线领导张唯一意外被捕,紧接着,机要交通员韩慧英也落入敌手,为防万一,“中央文库”紧急搬迁至小沙渡路合兴坊(现西康路560弄)15号的二层独立小楼,白色恐怖下,管理者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能艰苦地独立支撑。
1936年到1937初,陈为人等人终于找到党组织。因为陈为人病重,“中央文库”转移到中共情报机关徐强、李云夫妇手中。
1937年,徐强将管理任务交给周天宝。周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广有房产。“中央文库”搬至法租界顺昌里7号的花园洋房。
两年之后,因为顺昌里的一场火灾,周天宝紧急搬运文件资料。其时,正值日军占领上海的严酷时代,“中央文库”反复辗转于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乃至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具体地址不详,一度还回到过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
1940年,“中央文库”管理者改为缪谷稔,文件搬运至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立小楼,后又搬至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即缪的家 里。
1942年,缪谷稔病重,陈来生接管。陈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在日本军眼皮底下,将“中央文库”搬移至新闸路庚庆里过街阁楼,后租下成都北路972弄3号西厢房,门面是面坊,阁楼上存放着文件资料。
1942年,国共谈判之际,谈判代表曾将四分之一的文件运往延安。谈判破裂,运送无法进行,陈来生继续在面馆阁楼上保护文件。
1949年9月,陈来生将全部文件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我很想绘一幅地图,将“中央文库”在上海的历程,清晰地标明出来。但在日军统治上海的黑暗岁月,二十来箱文档反复跋涉,具体地点已然不详,那就得绘成多次震荡的曲线,犹如红军四渡赤水的形势 图。
那二十多年,是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在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上海,中共在自己诞生地的各种机构惨遭破坏,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地下组织的活动几乎停止,而中国共产党一批最为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能在这座城市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奇迹,不可思议的奇迹。
在阅读和思考中,我慢慢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那些坚贞不屈的战士:在不为人知的昏黄灯光下,在被死亡与酷刑笼罩的牢房中,在上海街头嘈杂的喧闹中,他们顽强地无声地战斗着,誓与党的机密文件共存亡——不,是宁可牺牲自己乃至家人的性命,也要把珍贵的档案传递到其他同志的手中。
他们只求奉献,并不希冀什么。但是,我们忘记这些无名英雄,是可悲的。也许,参与这场没有硝烟战斗的战士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但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真实而可靠地保存下来。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奉献的无比可贵。当为无名英雄们请功的文件上报之时,毛泽东把文件里的“有关同志”亲笔修改为“有关人员”,意思十分清楚,不管参与者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甚至仅仅是伸出手来帮一把的普通市民,均应该受到奖励,他们将永远被我们刻骨铭心地牢记。
(三)
秋日的早晨,我来到上海西康路,为了寻访“中央文库”曾经的隐匿处——西康路560弄15号。八十多年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中央文库”紧急搬到此地,那时,此处的地名为“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这里,并不是“中央文库”的诞生地,早期遗址位于现在的江宁路一带。在“中央文库”辗转二十多年的行程中,合兴坊15号是相当重要的场所,我想到这里寻访遗迹,是在阅读关于“中央文库”的大量资料后,明白它的重要价值,在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高层出现了顾顺章那样危险的叛徒之后,“中央文库”尚能生存下来,此处功不可没,是它守护党的最高秘密,躲过了严酷的时光。此处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因为其安全,被反复使用,直到日军全面占领上海,还曾短暂作为“中央文库”流转中的一个秘密据点。
西康路如今已经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几乎难以寻找到当年的痕迹。除了新建的高楼大厦,就是正在拆迁之中的工地,老房子、老弄堂、老居民,都在静静地消失、消散。时间紧凑,我一时竟然没有发现西康路560弄15号的踪迹。由于许多小型建筑和老式房屋被推倒,修建了体型庞大的高楼,建筑物的门牌号码遂显得跳跃和凌乱。我在那个地带闲逛,一幢高楼的脚下,我发现了一处色彩鲜艳、建筑相当可爱的幼儿园,它的号码是“西康路588弄36号”。我想,当年不惜牺牲性命投身革命的战士们,心底存放着的奋斗目标,不正是为了孩子们脸上能绽放幸福的欢笑吗?
从1927年早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就降临上海,那时,“中央文库”刚刚建立。由于最初设立时的严密制度防范,“中央文库”与党的其他地下活动有严格的分隔,它并未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白色恐怖迅速加剧,共产党的机构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中央文库”及其管理者,也被笼罩在可怕的魔影之下。顽强坚持到1935年,代表党组织单线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张唯一不幸被捕。事发突然,张唯一甚至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紧跟着,负责张唯一与“中央文库”通联的机要交通员韩慧英,也落入等候在张唯一家中的特务们的手爪。兵临城下,“中央文库”命悬一线。
“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陈为人,单兵作战,沉着应付危机。他相信自己的妻子韩慧英不会叛变,也相信久经考验的张唯一宁死不屈,但是,根据“中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保证机密档案万无一失,必须立刻转移。失去组织联系的陈为人,没有经济支持,也没有帮手,他伪装成阔气的老板,以每月三十银元的高价,咬牙租下合兴坊15号的独立小楼,随后,想尽各种办法,把几十箱文件,分散地搬了过来。其间的风险与艰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妻子韩慧英入狱,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陈为人照料。陈为人很快用完了仅有的资金,即使大人与孩子不吃不喝,那每月三十银元的租金从何而来?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陈为人难以获得可靠的援助。他想方设法,争取可能的扶持,一度甚至通过关系向鲁迅先生求援。最后,他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在乡下教书的妻妹韩慧如。韩慧如的出现,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获得一线生机,暂时脱离了绝境。韩慧如不但担负起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让陈为人得以专注于文档的整理,她随身带来的300银元的积蓄,也支撑了相当长时间的合兴坊的租金。在如此危险的环境里,每天深夜,陈为人躲进密闭的屋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细心整理几十箱材料,把零散的文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体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专业精 神。
他们终于坚持到韩慧英出狱,坚持到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严酷的环境,夜以继日的工作,彻底摧毁了陈为人的健康,党组织派人接过了管理“中央文库”的重担,并且把陈为人送进大医院治疗,但陈为人却想方设法逃避治疗,不愿意消耗党组织宝贵的资金。1937年初春,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陈为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经他系统整理过的“中央文库”的文档,留下了这位战斗者永不磨灭的印痕,他是倒在维护党的最高机密的默默无声的岗位上。
今天,当我们站在西康路560弄15号的小楼前面,我们回忆着陈为人和他的战友们。韩慧英在狱中受尽折磨,丝毫没有暴露党的秘密;韩慧如在经历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考验之后,成长为坚强的地下工作者,她协助秦鸿钧烈士,创造了上海地下党“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奇迹,这自然是后话了。
(四)
陈为人去世后,“中央文库”的管理,在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手中交接棒。曾经利用中共党员周天宝的亲戚关系,隐匿在顺昌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当时形势日益险恶,特别是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中央文库”屡屡遭受风险,秘密文档多次仓促转移,在上海租界的洋房、普通市民的石库门建筑甚至拥挤不堪的亭子间辗转。守护者们用生命呵护这批宝贵的文档,竟然多次化险为夷。1940年,“中央文库”的管理责任,落到缪谷稔身上,他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老缪”,是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对敌斗争的资历深,年纪并不老,与陈为人接受管理任务时年龄相仿,三十几岁而已。这又是一位呕心沥血保护“中央文库”,最后病逝在管理岗位上的共产党人。1942年,他重病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比陈为人离世的年龄仅大了一岁。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敌人严密统治的上海,要保护一大批党的秘密文档,风险之大,压力之重,苦难之多,绝对不亚于拿着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根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管理者必须以普通家庭的面目出现。老缪与陈为人的不同之处,他的妻子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老缪的妻子深明大义,默默支持老缪的艰苦战斗,从不多说多问,甚至老缪把收入抽出一部分,用以支付存放文档的房租,而自己家里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妻子也咬牙承受,不发出怨言。在日本人统治之下,他们断绝了各种收入来源,党组织也难以提供管理文档的经费,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为秘密文档遮风避雨。当妻子发觉老缪身体越来越差,想为他买些排骨补补身子,竟被老缪严词拒绝。关于导致缪谷稔病逝的原因,有一种简单的分析,说是受到肺病的传染。我却相信,那是坚守岗位的结果。为什么陈为人与老缪死于差不多的疾病?因为他们对于文档的整理和管理,是在极大的压力和极差的条件之下进行,他们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事,还随时支起耳朵,警惕外面任何异样的声响。那般恶劣的工作条件,那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和家人的压力,需要极强的意志来承受。管理者甚至经常烧着炉子,万一敌人突然闯入,准备点火烧房与文档共存亡。我想,他们最后染上严重的肺病,与那样的工作状况密不可分,他们是把生命奉献给他们所守护的事业。
“中央文库”历任管理者,均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可以描述,我选择陈为人与老缪作为代表,原因在于,这两位管理者几乎在差不多的年龄,患上大同小异的疾病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用共产党人的一腔热血,守护了党的最高机密。今天,走进我们的档案馆,各种各样的库房已经全部现代化,恒温恒湿,空气新鲜。回望当年,想到陈为人和老缪这些烈士,如何不倏然泪 下?
(五)
读者可能产生疑问,在敌对势力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两万余件绝密的文档,是如何“行走”的,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在上海滩喧闹的大街上实现来来回回的大转 移?
在我详细阅读有关资料之前,我同样有这种疑惑。当年的战斗生活,比众多描绘旧上海的电影,严酷得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们并没有汽车等工具可以使用,而满街遍布的特务军警,也不会像打闹片里的角色那般愚蠢。两万余件二十来箱资料,即使后来整理归并,其体量依旧不小。让它们多次穿街走巷而不被敌特发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奇迹的创造者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相当简陋或原始。比较阔气些的办法,就是雇用旧上海街头的黄包车了——那种在电影上看到过的靠人力拖行的车辆。当时,那是有钱人使用的代步工具。最初,在地下党还能够提供基本的经费时,陈为人他们为了遮人耳目,雇用过黄包车搬运文档。
后来,情况的变化,形势的严峻,经费的短缺,连黄包车的使用也难以为继。
以最后接棒的管理者陈来生的故事为例。与陈为人、老缪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老资格革命家相比,陈来生很年轻,接棒时才二十三岁。1942年,老缪病重,党组织不得不选择新的“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选中陈来生,除了他年纪轻轻便闯荡过大风大雨,是经历过严峻考验的战士,恐怕也是看中了他的年轻力壮。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租界。老缪原来保护文档的秘密处所,危机四伏,但是,要把那么多秘密档案转移出租界,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日军眼皮下通过,简直无法想象。年轻的陈来生,一直在底层拼搏,有底层市民生存的方式。他动员自己的家人兄弟,以挑担货郎走家串巷的方式,以破篮子、面粉袋为工具,甚至以偷运粮米的“跑单帮”形式,蚂蚁搬家似的把两万件文档偷运出了租界。他们的英勇无畏,让后人感叹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命运眷顾了这些特别的战士。笔者的祖母,当年也居住在上海。听她说起过,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没吃的,活不下去,只能跟人去乡下买米,夜里钻铁丝网爬过封锁线。她说,同去的人,不少被打死,她命大,活了下来。陈来生他们的偷运,不是一天两天,是整整一个多月,只要其中一次出了差池,后果就难以估量。
陈来生把文档偷运出来后,开设一个面坊,阁楼上藏着那些宝贵的文档,如此一直坚持了七年,熬过抗日战争,熬过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黑暗,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解放。其间,依据延安的指令,陈来生抄写过秘密文件,还协助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将一部分文档运到了延安。
(六)
八十多年前,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关心“中央文库”的安危,希望瞿秋白同志起草管理制度。瞿秋白同志认真地撰写了管理条例。“中央文库”能够屡屡闯过险关,是管理者们严格执行管理规矩,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结果。今天,我们回忆瞿秋白撰写的文字(陈为人题为“秋白遗笔”),惊叹不已的,不仅仅是瞿秋白思维的缜密,还有他处变不惊、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心怀,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信心百倍地告知大家,保护文档的目的,乃是“备交将来”。
今天 ,身处瞿秋白所说的“将来”的我们,在每天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中,当你静下心来,阅读和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是否感受到前辈革命家鞭策和激励的目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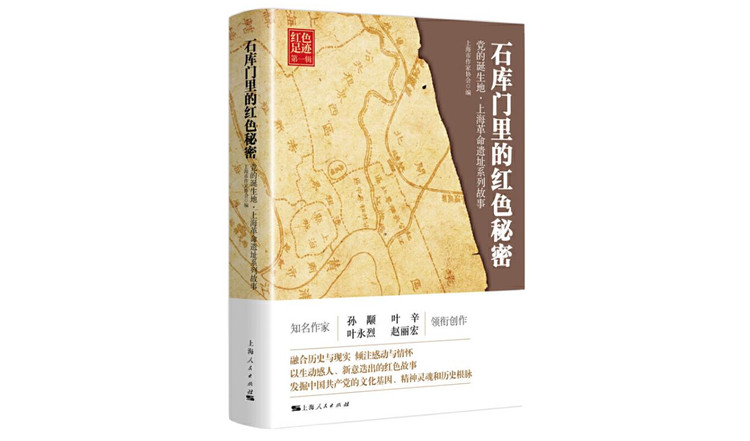
作者:孙颙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本文摘自《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