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出版社新近同时推出吴亮和程德培的评论集《或此或彼》和《黎明时分的拾荒者》,或许是为了促销,出版社还特意为这两本评论集制作了一种合并销售的套装版并将他俩上世纪80年代在《文汇报》和 《文汇读书周报》上轮流 “坐庄”的专栏短文以《文坛掠影》为名结集成册作为馈赠礼品。坦率地说,这三本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本人过往都已拜读,但看到套装后还是忍不住先拿起《文坛掠影》翻阅起来,因为那些精炼直率的文字足以唤醒自己对80年代那段美好的记忆。
《文坛掠影》收入两位作者对文学新作的快评凡113则,每则篇幅大都在800字以内,这个名为“文坛掠影”的专栏每周一次,前后持续两年零四个月。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尽管足可见出吴程二位风格的鲜明差异,但又至少传递出三点高度相通的气息:一是作者的韧性,每周呈现出来的虽只是在800字以内,但背后的阅读量则肯定是它的几何级数,而所评作品无一不是绝对的新作;二是视野的开阔,体裁囊括大部分文学样式,作家既包括在当时知名度颇高的名流亦有初出茅庐的新人,作品既有中规中矩的传统写作也有充满实验探索特点的所谓先锋之作;三是文风的干净率直,800字的篇幅要立得住一定来不得半句废话,肯定的当然不会掩饰自己的喜爱,否定者则是单刀直入刀刀见血毫不留情。正因为此,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所承载的内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沉甸甸的:在信息传播上它是当时文坛新作的一份快报,在文学批评上它是“酷评”美文的一个样本,在溢出效应上它是那个文学美好时代的一段折射。
不妨顺着那个文学的美好时代往下说。

吴亮和程德培是上世纪80年代初并肩冒头成名的两位批评家,几乎完全不同于现在一拨又一拨接踵而至的“学院派”批评。这两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而是从工厂直接走进“作协”系统的批评“另类”恐怕也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就是这两个 “非学院派”的批评家,其个性、其特色却绝对不是“非学院”,在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上甚至比所谓“学院派”更严谨更规范,他们分别为自己烙上了印记鲜明的“识别码”。
初“识”吴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文学》和《文艺评论》上不时能读到他那副题为“一个沉湎于思考的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的系列论文。这个系列对话当时读起来虽有些“烧脑”,但还是很心甘情愿地被“烧”,因为它完全不同于通常看到的那种为对话而对话的所谓“对话体”,而是真正的两颗不同脑袋的对话,是两种思想的碰撞。作者运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将各方观点陈列出来,将其中的矛盾抽丝剥茧般地逐层揭露,从而将讨论引向深入。坦率地说,那些个“对话”当时虽未必完全能够理解,但的确是为这人的思辨能力而留下了深厚的印象。随后不久见到吴亮其人并随着交往的深入,面对那颗硕大的脑袋,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这颗大脑袋真的不安分,在文学批评之外,一会儿转向艺术批评,一会儿又写起了小说,但无论他干什么,超强的思辨能力这一点则是贯穿始终,新出版的这本评论集也不例外,单是《或此或彼》这个书名便可见出一斑。也正是在这种强大思辨力的驱使下,这本论集中提出了许多鲜明的观点迄今看来也还是耐人寻味的,比如“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先锋就是历史上的一座座墓碑”“要么畅销要么沙龙”“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速朽一代”……而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析中也不例外,比如在谈到莫言时,吴亮写道:“莫言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拥有极大可能性的小说空间,在那里失去了优雅与节制,只有生命之流和感觉之流浩浩荡荡泥沙俱下地向我们涌来……我们有理由对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示轻蔑,但是却回避不了莫言这个人对我们现有文学秩序和优雅心态的扰乱。这种扰乱是有着革命性的,它的意义可能要到几年后才能被承认。”这段文字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其中的逻辑联系十分严谨,虽以判断语为主,但这些个判断大都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这或许就是逻辑的力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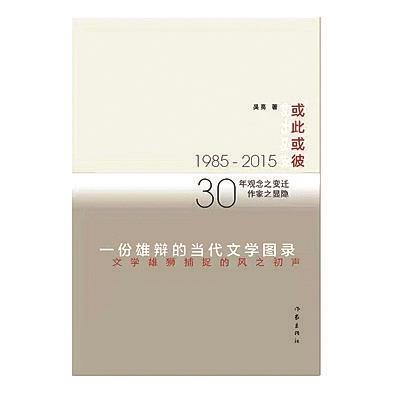
“识”得程德培同样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各种文学杂志上,不仅是因为他经常与吴亮轮番出现,更是因为他的批评往往切口不大且更多地关注作品的“技术性”问题,这在以“宏大话题”为主流的那个年代真是不多见的。接下来在上海作协的一间办公室中同时见到吴亮和德培时,德培的头颅虽远不及吴亮那么大,但笑眯眯地盯住一个人的时间则远比吴亮要长得多,处事也相对要细不少。当然以此来认定德培批评特色的成因当然是一种玩笑,但在《黎明时分的拾荒者》这本评论集中,37万字的篇幅不过只是评论了15位作家,平均对每位作家评说的长度为近两万五千字。这当然只是一个平均数,而实际操刀时对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批评其长度还是有不少差异,比如对李洱批评的长度近六万字,对吴亮《朝霞》的评论长达三万字,但即便是短的也有一万五千字。我自然不会以评论文字的长短论英雄,事实上也真有不少评论文字固然很长,但注水的成份却不少。而看德培的评论,其绝大部分文字无不都是紧贴作家作品的实际:作品论绝大部分都是对作品文本实际的条分缕析,尤其注重所谓形式的特点;作家论则是将评论对象的主要创作历程进行梳理比较,看其连续性及差异变化的轨迹。德培后期的批评虽也有一点引经据典的文字,但他的引用同样还是为了对作家或作品的某种艺术表现进行解析,同样是紧贴着作家作品的实际而不似其他某些评论的引经据典,不过是在那里自说自话式的炫技而已。记得有一年在上海书展期间与德培聊天,当时他正在准备评论阿来中篇三部曲“山珍三部”的写作,闲谈中发现为了这篇评论他差不多是阅读了阿来的全部作品,其熟悉程度足以信手编撰一张“阿来创作年表”。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死功夫笨功夫,但对评论而言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最基本的功夫。事实上,我们读评论文章,写作者是否认真研读了原作在他的文字中总是会露出蛛丝马迹的,如果连文本都没有认真地读,这样的文字实在是不能称其为评论的。
一个长于思辨,一个精于细读,当然不是吴亮与程德培评论新作的全部特点,我之所以突出强调这些,固然是因为这既是他们批评的鲜明特色,更是文学批评本应秉持的基本素质。如果不讲逻辑的缜密不扣概念的严谨不读文本的自身不顾作者的整体,这样的批评和作家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遗憾的是这样的“不”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亮与程德培的批评才见出其价值与可贵。我尽管也可能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评判,但其基本功的扎实和学理的严谨则是永远值得尊重的。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卫中
*图片来自pixabay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