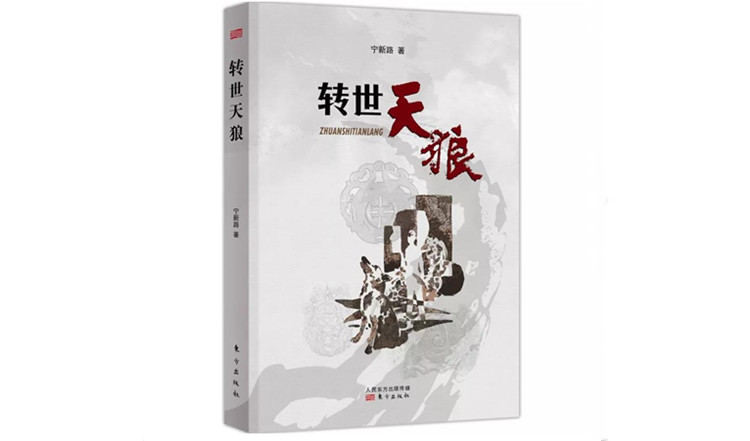
《转世天狼》是作家宁新路的长篇小说新著。仅从作品的命名来看,便自然使人觉得新奇而欲知其内容为何。我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先睹为快地看完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从表面上看,这部从书名到内容都概不常见甚至有点荒诞的作品,但如仔细加以品咂,便会感到在表面上很可能是根据一个民间传说所演绎而实质上包含着发人深思的人生世相;其独特的揭示方式仍能够给人以启智的警示。因此,我觉得不妨将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将民间传说与人生况味相揉合的奇幻小说加以赏读。
作品的基本表现手法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方式。全书出场高密度的贯穿性人物是开玉作坊的柴大老爷与他的看门管家张鞋娃;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则是张鞋娃的亲密伙伴——一条叫阿黄的看门狗。从表面上看,柴大老爷与张鞋娃乃至阿黄之间是绝对的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却又不那么简单与单一。那个浑身散发着臭鞋味张鞋娃,却能在偶然的情况下被柴大老爷收纳和使唤,肯定在他下三赖的表皮之下还有某种“过人之处”。甭说别的,就是那条非同寻常的看家狗阿黄,一般人它都不给好脸色,可唯对张鞋娃却破例的忠顺(可能内心里也服气)。这除了狗与人之间也有某种“惺惺相惜”之外,骨子里也有强烈的磁场能够撞击出火花来。但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柴大老爷主要还是为了张鞋娃便于驱使,可以随意打骂,乃至当成一件宣泄器具,自觉比较靠得住,所以就连嫖娼时也带着他,以便随时听候差遣。但张鞋娃却能“闲中偷忙”,他也抽空借机找乐。作者的深刻之处就在这里,他在对人物的刻划上,从不那么简单化,浅表化。否则,如果只将柴大老爷和张鞋娃之间处理成黄世仁与穆仁智那样一个暴主一个恶奴的主从关系,那张鞋娃也就不是“天狼转世”了。但他们之间也并非一般的狼狈为奸,而是一种层层相叠、环环相扣、相互扭结、难解难分的离奇而又真实的人物关系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作者独具匠心配置与创造。
奇幻吗?有一点,却又如见其真;荒诞吗?一切却又触手可感。柴大老爷的发达绝非凭空而来,同样有其深厚的背景和他人难及的优势;这里有百年几代的精于经营,有凶残到家的盘剥手段,更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国家不幸邪幸,在柴大老爷和他的玉作坊的背后,有日寇派驻军官,甚至连日寇军官小野“宠幸”的妓女小菊花也优势“借横”;还有柴太太娘家近亲伪政府官员撑腰……这才能使柴大老爷发迹的图谋无不成功。但同样是,作者并没有将作品处理成一般的剥削压迫“模式图”,而仍然是通过张鞋娃、阿黄等典型化特征性的描写,凸显了权势方花样翻新的酷虐。如对玉作者的苦工们无孔不入的榨取、作贱人格的隐身搜身……在这当中,作者绝未忽略了张鞋娃与阿黄犬的“神功”——所有的重要角色在节骨眼上绝不会缺席。
善恶兴衰的转化规律在任何创作方法的作品中也不可能截然相反,即使在带有某种荒诞色彩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基本内核仍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小说中的柴大老爷挖空心思,翻云覆雨,“事业”运作与狂浪享受双相并举,似乎有无限精力远涉四方,一为玉业,二为猎色寻欢,除在他的基地有本宅家室之外,在新疆和田,在云南,在太原,在南京,都有“小家”和妻室。但到头来,由于“自窝乱,自窝反”,还有此起彼伏的外忧,这位精明强悍的大老爷,最后由于伤病交加,虽然竭力挣扎,终也未能战胜命运的惩罚而呜呼衷哉,未能逃脱“自作孽,不可活”的结局。他遗下的除了玉行家业,还有无一缺额的几个女人。
但“转世天狼”张鞋娃仍然健在,也许是因为他虽也有诸般劣迹,但灵魂深处仍存有一个纯朴尚善的角落,心目中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女人小莲。这个小莲在作品中虽“戏份”不多,却始终是这堆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罕有的比较干净的灵性亮色。还有,那条阿黄老狗,尽管瘦弱,还是又回到了张鞋娃身边;结尾有一段文字意味无穷,不可不引:“张鞋娃由他的老狗阿黄陪伴,等小莲回来,日子过得平静而快。可等心上人的日子,却是焦心的,等得人和狗,越发凄怆,而他仍然等她(从尼姑庵)回来,虽等待回来的期限无限,但他感觉等得很幸福”。
本书在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上与其内容非常谐合。语言文字生动舒放,生活化,个性化,色调浓郁;某些方言上语用得适当贴切。有些虽有些俚语恣肆,但憨直中含机趣。作者显然是追求一种泼辣率真,富有性格化的格调,也是一种不乏探索精神的尝试。在谋篇和结构中,同样是以一种旨在生趣活络而忌呆板滞涩的方式进行组合。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值得赞赏的表现。如在交待柴大老爷设置四面八方的“家室”时,有意以回报几乎相同的文字加以点染,读来不觉其重复乏味,反而觉得在调侃中含有讽刺意味;同时也反而省却了许多笔墨,增强了艺术表现的张力。
作者:石英,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