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自1987年牙买加作家奥利夫·塞尼奥尔首次获“英联邦作家奖”以来,牙买加文学在全球文学场域愈发为人瞩目,逐渐从“加勒比海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分支进入国际读者视野。
其中,《女王案》是牙买加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全书结集多篇小说,都是当下活跃在牙买加和加勒比海文坛作家的代表力作,包括现代牙买加文学运动开创者奥利夫·塞尼奥尔、阿莱西亚·麦肯齐(曾获英联邦文学奖)、威尔玛·波拉尔德(曾获美洲卡萨德奖)等。现分享书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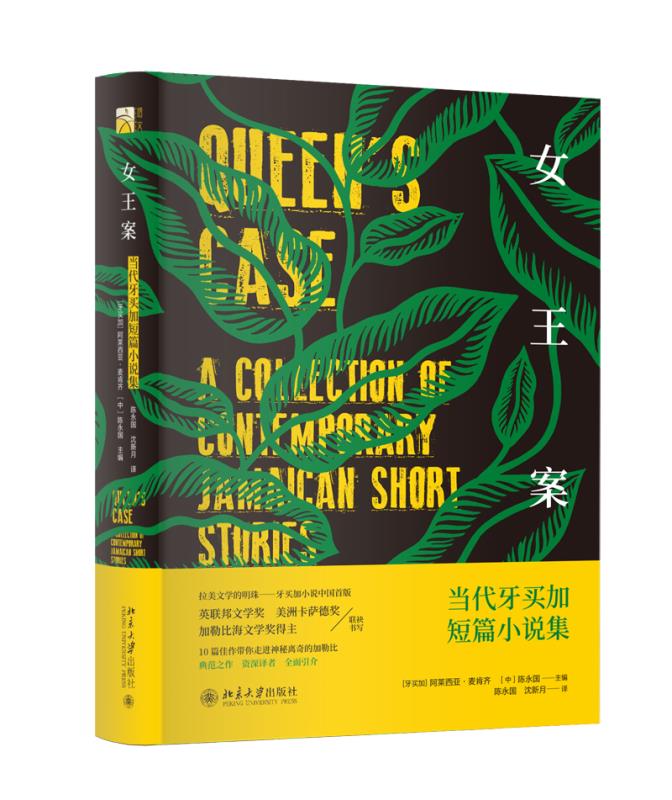
《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
[牙买加] 阿莱西亚·麦肯齐 等 著
陈永国 主编
陈永国 沈新月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除去博尔特和潘趣酒,我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方面了解牙买加,比如小说。没有什么比寒冬孤独的夜晚,看一本来自加勒比海的故事更舒适的了,不仅因为这个国家温暖潮湿的气候,更因为这些故事里绵密交织的情感,你急着想了解的殖民史,还有他们似乎与生俱来的身份与性别意识。
我手中的《女王案》是国内第一部牙买加短篇小说集,编者在每篇小说前,都附有一则简短的作者介绍:他们或已定居国外,或有着长年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也许牙买加太小了,不小心就出了国?其实关键在于牙买加人的文化杂糅性:国家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黑人、西班牙统治者、英国、法国、荷兰等争夺者的文化似乎混合成了天然基因,为当代牙买加带来了必然焦虑。
阿莱西亚·麦肯齐将它称为“后殖民标签”。有记者问麦肯齐是否反感“后殖民地文学”这个标签时,麦肯齐回答:她作为一位作家,在写作时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在写后殖民地文学,她只是在写自己的故事。诚然,当单单阅读某一位作家的创作时,我们确实在阅读个人故事;而当我们阅读某几位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作家创作的时候,我们阅读的就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国家叙述以及当代表达。
一
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小说:奥莱尔·塞尼奥尔《女王案》中“我”的舅舅从英国留学归来,但是到底学到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文凭之类的佐证。唯一能从侧面反映出舅舅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就是他那从不离身的圆顶礼帽、拐棍、手套以及一个绝不示人的箱子。他每天下午四点前准时出门,用深沉悠扬的声音打招呼,僵直地走上通往大路的小路,从不错一个节奏。人们开始只是认为也许重归故土的舅舅还需要些时间适应,但时间一长,人们的看法就慢慢改变了。直到有一天舅舅把“我”叫到屋子里,说:“我早已没有心脏了。那是他们装在我身体里的机械装置……我在那里住院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小心脏拿出去了……我从来没有让他们这么做……这是最高犯罪。”打开舅舅的箱子,里面保存的全部都是写给英国女王的寻求正义级的的信。女王真的偷偷地取走了舅舅的心吗,当然不是的。“心”就是舅舅乃至牙买加人的精神世界,留学海外的舅舅敏锐地发现了,西方文化已经彻彻底底地改造了他的“心”,他自己却无能为力。
牙买加人发现,虽然殖民已经结束,但是精神上的统治仍在继续,更可悲的是,这已经深入他们的血肉之中了。所以他们面对国家的贫乏,精神的奴役,难以不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怨愤。小说中的“舅舅”则是作者手中的钝刃,指责那些文化殖民者偷走了他们的“心”。
如果说,《女王案》隐含着对牙买加殖民历史的控诉,那么其他小说也或多或少在表达着这样一个加勒比小国,在宗主国离开之后的惶惑、游移和茫然。《爱的最后一位使者》中费舍先生要感谢美国人给他签发了(他)在他自己国家的工作签证,头衔竟然是“外国专家”。《穷途末路》中女主人公感叹一张本地的身份证是你作为人类一员的凭据,而怀中的蠢狗却正依仗自己的品种得到宠爱。《基石》中“我”和“我”的母亲相互依偎着躲在千疮百孔的屋子角落,以躲避这场横扫一切的暴风雨,而 “破屋”和“暴风雨”正是牙买加与西方文化的最好象征。
不过,牙买加作家并未就此终止,面对荆棘密布的文化重建之路,粗浅的讽刺甚至偏见式的指责并不稀奇,小说中最珍贵的是他们在描写那些有机会融入西方社会的人物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做出的决定。
《女王案》中“我”的舅舅在因为留学而发疯之后,“我”本应该离我的舅舅远一点,或至少对留学这条道路更加谨慎,但事实上,“我”读完高中之后,获得了去英国读大学的奖学金,姥姥为“我”的成功高兴得哭了,唯一嘱咐我的只是不要像舅舅那样太过努力了。“我”继续走上了“发疯”的道路。《穷途末路》中特莎娜没有随他们国家的大使一同被召回,而是非法地居住在比利时,冒着被抓的风险做着保洁的工作。虽然她看不惯身边人的虚伪,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愚蠢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她吐槽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在面对她口中的“蠢妇”为她提供的护照和身份证时,她自顾自微笑起来。“不,埃洛尔,我才不是穷途末路的那个。” 作家没有单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对人物做道德化判断和描绘, 相反,作家真实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更好的生活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民族与国家也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更何况如果放弃,你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遍地杀戮、遍地偷窃的地方”。

二
阿莱西亚·麦肯齐在面对采访时说到,在编这本书时考虑了性别的问题,让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数量五五开。虽然男女作家的占比是编者刻意保持的平衡,但是无疑,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还是独见风姿。
在几位女作家笔下,小说中的男人总是不约而同地退场或者缺席。莎蓉·利奇《父亲般的人》,讲述了小女孩翠西与帕尔默先生之间的故事。翠西的父亲身材高大,膀阔腰圆,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口齿伶俐且聪慧敏捷。帕尔默先生不仅块头巨大,外表还总是不加遮掩地脏乱——衣襟半边耷拉在裤腰外面——毫不体面是他的一个大问题。他的头发永远都像没梳理过,碎屑状的灰白胡子卷叠成团,里面勾缠着的食物残渣粒粒清晰可见。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之下,翠西本应对帕尔默先生置若罔闻,但是她却对帕尔默先生有一种出于家人情感的保护欲望。
翠西细腻的情感将一位缺失父亲的少女心绪展现得淋漓尽致,女孩子难言的感受融进灯光黯淡的屋子里,悲伤幽幽地从窗缝渗出屋外。单纯地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少女的情愫无可厚非,但如果联系起牙买加的社会,也许帕尔默先生就不单单是一位邋遢的好人了,他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言人。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是家庭的根基,他的缺席正是对牙买加复杂殖民历史里根源性文化缺失的隐喻表达。
或许莎蓉·利奇正将每位牙买加人的精神内核——“翠西”——提取出来,借着翠西对帕尔默先生的一往情深来表达自己,乃至所有牙买加人对祖国根源性文化的渴望,也透过女性书写,让我们看到愤怒背后的,更为浓郁的忧伤。
一部小说集,如果仅有忧郁的女性,未免以偏概全,这里面,也不乏充满高昂女性意识的作品。第一篇小说《玛丽玛》中,全篇都通过不同的女性进行讲述,难觅任何一位男性的踪影,当房屋燃起大火,冲进火海救人的同样是女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玛丽玛》中充满着色彩对视觉的冲击。一身长长的白色睡袍,黄色的辣椒田,仿佛上过糖釉的蛋糕似的亮闪闪的皮肤,红的、黄的、蓝的玻璃珠手链……每个细节无不体现着女性视野下对色彩的敏感。《辛迪的写作课》讲述了一堂写作课上的情景,主人公“我”和写作老师辛迪都是女性,而当辛迪让“我们”去书写曾经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一天这样一个话题时,“我”所写下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尾,“她刺死了男朋友。他死了。”故事结束了。他死了,她活着;男性死了,女性活着。也许故事并不是目的,麦肯齐鼓励笔下的女性开始创作,随性表达自我,从小说体裁中托生出来,最终归于伟大的诗歌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目的。
三
抛开来自遥远的加勒比海的浓厚情感,在小说创作方面,牙买加作家也实验了许多独特的创作方法。
《玛丽玛》虽然只是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通过新型创作方法的采用,使得这个简单故事以多棱镜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中每一个段落都仿佛折射了不同的光,以该段落叙述者的名字为小标题,以不同的叙述角度展开,令读者进入了一个换位、多元而立体的世界。主人公玛丽玛又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作者就分别用“玛丽玛”与“小玛”对这两种人格进行区分,解决了描写这种特殊人物的困难,为读者展示同一肉体,双重灵魂的存在。
另外有趣的就是《爱的最后一位使者》。虽说作家是个男人,但是你总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对男性的一种讽刺。费舍先生算是个成功人士,身边也从不缺乏女人相陪,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位能长伴左右。这篇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提供了类似电影一样的“闪回”画面。
“费舍先生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海伦时的情景”。
“桑德拉走后,费舍先生回想起他和海伦的那段恋情”。
“那天夜里,费舍先生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不断浮现出他和海伦之间的往事”。
“费舍先生回想起海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表白”。
“望着玻璃上流淌的道道雨水,他想起了最后一次与海伦见面时的情景”。
当我们沉浸在费舍先生对海伦无尽的回忆中时,我们敢肯定费舍先生一定深爱着海伦,并出席自己所爱的葬礼,而结果,费舍担心雨天他的汽车底盘会漏水进来,所以费舍再一次用回忆的方式哀悼了自己的旧爱。不是拜这种重复的结构所赐,也许就没办法更好地体现费舍“渣男”本性吧。
《女王案》就是这样一本短篇小说集,将地处遥远的牙买加社会中的忧伤、焦虑、愤怒、迷惘、希望,夹杂着欲说还休的历史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一股脑地倒在你面前。
作者:焦洋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李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