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间2月9日,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幕。
韩国导演奉俊昊和他的《寄生虫》,成了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四大奖项。
这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奥斯卡。
《寄生虫》也成为了奥斯卡历史上首部获得最佳电影奖的非英语片。
关注社会政治、关注阶层、关注种族……已经成为奥斯卡心照不宣的“择偶标准”。
而这部成为韩国之光的《寄生虫》,几乎就是为奥斯卡而生的,是一部赤裸裸的“韩国折叠”。
大部分情况下,贫富差距无论有多对立,两极的人类只是静默的对立,只是平行世界互不侵犯的仇视。
就像是导演奉俊昊曾在采访里说:“虽然生活在一个国家和城市,但富人和穷人可能都没机会相遇”。
而《寄生虫》偏让这两拨人相遇了。
一座豪宅,暂时让渡给穷人做一次豪宅主人的白日梦。
梦醒的时候,富人彬彬有礼的教养下再藏不住骨子里的傲慢,穷人蟑螂一样见不得光的小日子也不再过得理所当然。
1、底层困境
耍尽聪明找到一份好工作,也摆脱不了一辈子的穷命。
韩国底层穷人到底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一家四口,半地下室的窗外,常年飘逸着醉汉留下的尿骚味;
电话停机、上网靠举着手机到处找信号去蹭;
全家人集体失业,主要收入来源是靠折披萨盒子的兼职为生;
一个卫生间的标志是高出地面两三个台阶的马桶,弯腰上去再弯腰下来;
不肯关窗,特意邀请大街上臭烘烘的消毒剂洒到房间里来顺道杀一杀虫子——因为家里的虫子太多了,就当免费杀虫大扫除了。
宋康昊饰演的爸爸金基泽刚才在就着水啃干吐司的时候,就顺手弹走了一个。
电影开头就是这扇窗子的视角,墙角一袋又一袋的生活垃圾,与你眼睛齐平的水平线上,奔跑着卷着尘土的车轱辘,一家人的袜子吊在这扇窗户旁转来转去。
这个视角看出去,不像是人类的视角,更像是一只蟑螂的视角。
人类的视角,我们总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窗外是绿树成荫的庭院,户外桌椅上洒下午后懒散的阳光。
而这样的一幕,儿子金基宇就在自己的家教课雇主的家里看到了。
他还领略过抱着狗的贵妇女主人,头脑简单容易上钩的傲慢。
女主人要的高级别老师,不是指成绩上能让孩子实现飞跃的,而是切实能震住孩子,能在某种力量与精神层面让孩子完全五体投地的“名师”。
蝼蚁底层的市井聪明,足以让基宇对付起这种脑中空无一物还要力求彰显格调的上流人士来,游刃有余。
所以,他很懂得在女主人的公开监视下,对她女儿多慧展开心理攻势这一套。
更能在女主人说起自己给小儿子多颂找了N多美术老师都无一例外得撑不过一个月时,第一时间敲定妹妹基婷作为人选,并迅速通过学生多慧口中形容的弟弟故意表现出的艺术癫狂与突然抬头仰望天空几分钟的特征,来帮助妹妹制定一套可以降服小屁孩的更高段位方法。
基宇的聪明与反应速度,不止于此。
他还会通过学生多慧对于基婷身份的怀疑,与一句嘟起嘴来的反问“杰西卡是你女朋友吧”,就能迅速断定多慧对他有意思,并在多慧抓住他手的一瞬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抓住机会,亲了下去。
几乎没有一秒的犹豫。
光速打脸了好朋友对自己的托付和信任。
而且,这家有钱人,真如好朋友交代的那样,“非常单纯”。
不光是女主人,全家都是如此。
既然如此,那我何不趁机拿捏住多慧的心,说不定还可以成为富人家的女婿呢。
基宇一家人,都是求生技能满分的“聪明人”,多慧全家,都是没被社会毒打过思虑单纯活该被骗的“蠢货”。
可社会阶层不会因为你全家都具备小聪明就天降大别墅,也不会因为富人计较的少就停止让他们越来越富的步伐。
穷人这辈子想进别墅坐一坐,可能最合法的方式就是为别墅的主人工作了。
于是,这一家子的贪婪,从儿子见识过别墅外的风景后,就再也刹不住了。
他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别墅中的司机、女仆这些难得的肥缺一举弄到手,他们要让别墅的男主人朴社长给基宇全家人发工资。
为此,他们不惜挤兑同阶层的另一群人。
只是因为互不相识,就认定我家人的生计比你的生计更重要。
基婷故意往原雇佣司机车里丢下自己的内裤,让男主人朴社长在坐车时不经意发现,并引导他往司机带女人在自己车里做出车震这种肮脏的事情来,以让其丢掉工作,把这坑,留给正在奔驰4S店里熟悉驾驶高档车辆的爸爸。
通过多慧从不允许吃水蜜桃的消息,了解到前管家水蜜桃过敏的核心信息,并找准时机通过故意在管家身边撒水蜜桃毛的方法,让其狂咳不止,并诬陷其是肺结核,让女主人忌惮,而为母亲忠淑拿下了最后一个“工作空缺”。
如此齐心协力、机智聪慧的一家人,却摆脱不了底层穷人的命运。
他们趁着主人全家出门露营,像分食面包屑的昆虫一样,迅速奔走相告聚集在客厅里。
躺在灯光下的沙发上,躺在夜空下的草坪上,四仰八叉,把酒交欢,畅想自己成为这家人的亲家,鄙夷这家人都很好骗,大言不惭地说这就是他们自己温馨的家,甚至调侃说,万一朴社长一来,丈夫金司机会像蟑螂一样躲起来。
戏剧化的是,门铃响起的一瞬间。
他们真得如自己调侃那般,迅速四散而开,趴在见不得光的角落里,又做回了蟑螂。
穷人用尽全力为全家老小找到了工作,还以为从此过上截然不同的一生。
等大梦初醒,才知道这偷来的上流人生,原来还是要还的。
等灯光一亮,午夜的钟声一响,原来蟑螂还是要滚回到湿漉漉的阴暗角落里去。
2、“味道”的囚徒
你洗得掉衣服上的汗臭味,却洗不掉骨子里的穷酸味。
在草坪聚会上,金司机为何要突然临时起意捅死朴社长?
何至于此?
很多人在这个剧情突然发生的时候,会有一种蒙圈的疑惑。
朴社长是有些冷漠,也是有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在里头,但这都是人性里最基本的。
这样一个勤劳养家,呵护妻子,关爱孩子,出手大方,连劝退家仆都要讲求委婉优雅不揭人“伤疤”的男人,没有大奸大恶,没有言语过激,为什么金司机要一刀捅死他?
因为气味。
只是因为,他向妻子私底下讲过,金司机身上有着一种奇怪的气味。
在那个“蟑螂”狂欢派对戛然而止的夜晚,多颂不敢住在屋子里,坚持去庭院里露营,为了保障多颂的安全,朴社长提议,跟妻子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因为从客厅的落地窗望出去,刚好可以看到帐篷里的儿子。
只是,在客厅大茶几的底下,趴着几只躲在阴暗处的三只“蟑螂”——基宇、基婷、金司机。
于是,夫妻之间私底下不经意的聊天,就被金司机听到了。
朴社长抽了抽鼻子,说自己似乎闻到了金司机的味道。
这是朴社长第一次跟妻子提起这种味道,妻子嗅了嗅,这个时候的她,说,没闻到。
丈夫告诉她,这是一种葡萄干放久了的味道。
确切点说,是买不起私家车只能每天挤地铁的底层穷人特有的味道。
所以,这种味道,并不是某种具体的气味。
而是上层人士骨子的傲慢与鄙夷,让他闻到了下层人身上的某种“穷酸味”。
所以,妻子在他解释之前是闻不到的。
但当她被老公暗示了这一点之后,她的嗅觉就不再“客观”了。
儿子的快闪生日会上,她安排金司机拉着自己去采购东西。
回来的路上,她给自己请的宾客打电话,寒暄过程中,她也“闻”到了这种特殊的味道。
于是用手挡着鼻孔,皱了皱眉毛,但这种味道似乎越来越浓烈,以至于她赶紧打开了车窗,好让这种“穷酸味”赶紧散出去。
金司机察觉到后,下意识到侧过身子,闻了闻自己的衣领。
于是他慢慢回过神来,目视前方的时候,他似乎隐约明白了,朴社长提到的味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了。
金司机从一开始,就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自己可以跟雇主朴社长平等对话。
他向朴社长介绍自己从前的工作时,得意地表示,自己这个工作,是一种“陪伴”。
还会在朴社长吐槽自己太太不会做家务的时候,主动“安慰”对方,但您还是很爱她,对吧?
还好他适可而止没再追问,才保住了朴社长认为一个下等人该有的分寸与边界。
朴社长所介意的边界,是下等人永远不能僭越主子私事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工具就干好工具本身的分内之事的冷漠本质,是永远拒绝跟穷人平等对话随意交心的傲慢。
但金司机,还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他内心的自卑,总是不自觉地要通过某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去拉平。
在多颂的快闪生日会被以加班的形式邀请到现场帮忙的时候,他误以为参与了朴社长家的“私人活动”,就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跟他对话:
您也很努力呢。
也是,毕竟您爱她。
看似是两句普普通通的闲聊天。
实际上,刚好碰触了朴社长最忌讳的界限。
员工反过来评价老板很努力?你有什么资格?
我爱不爱我老婆这是我的私事,轮得着你一个家仆在这说三道四?
朴社长当即不悦,再次跟金司机明确道:
金司机,反正今天就算加班,你就当作是工作好吗?
什么意思?
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我付你加班工资了,一个家仆,一个工具,领了工资就把事儿办好,别在这评头论足、多嘴多舌地做出不符合你身份的事情来。
至此,朴社长明确划清了自己与金司机之间的阶层。
而且这个阶层,永远不可逾越。
不要以为你洗掉了衣服上的汗臭味,我就闻不出你身上的穷酸味儿。
不要幻想,你成为我的家仆,就误以为成了我的家人。
当朴社长捏住鼻子忍着恶心从前管家老公的尸体下翻出钥匙,准备送儿子去医院的时候。
金司机给出了他的死亡凝视。
因为,这个时候他十分确定了一件事就是,他和地上这具满身是血还不忘向朴社长致敬的谄媚尸体,才是一路人。
而他们,无论进出这个家多少次,为这个家的主子做过什么,都只是主子眼中,永远散发着穷酸味的蟑螂。
这对底层穷人来说,是最暗无天日的恶意。
底层穷人恨极了这种暗无天日的恶意,但却无法找到改变的办法,只能拔刀相向,砍了下去。
本可黯然苟且,但偏偏有人揪住他的耳朵提醒他,你不配。
尊严被捏碎的时候,人类便容易杀戮。
这种挥之不去的味道,收下了终生囚徒。
3、粘人的石头
不甘的贪婪,会驱使人丧心病狂地向下争夺。
敏赫给基宇家送来了一块奇石作为礼物的时候,告诉他们,这预示着好运。
而自从这块石头进门后,全家人的命运似乎都开始转好。
大雨淹进地下室的那天夜里,他们刚完成了在主人别墅里狂欢完毕的疯狂逃窜。
一场大雨带给别墅区富人的,只是露营泡汤,“但可以开派对”。
而带给地下室穷人的,是整个家都泡在肮脏的泔水里,马桶像发神经一样喷张着令人绝望的黑水,全家人无处安身,所有穷人都湿漉漉地一起挤到体育馆的地板上睡觉。
富人的聚会,是衣帽间悠然自得的小曲和镜子前换完一套又一套。
穷人的狂欢,是街头大喇叭下的优惠大酬宾倒计时与蓄势待发的哄抢。
富人之上,还有更富的人,他们正在草坪上狂欢。
穷人之下,还有更穷的人,他们主动把自己囚禁在地下室,四年没见过阳光,每天还在开开心心张着嘴巴等着主人的施舍。
基宇站在多慧的房间,望着窗外草坪上奔跑着的富人,想着脚底下比他更穷的穷人。
突然失神地问多慧:“我适合吗?”
在他眼里,这些人接到一个朋友的聚餐电话,随随便便就可以衣着得体地提着礼物融入到富人的狂欢中去,而他为了能答应多慧的邀请,他需要想尽办法处理干净身上的又湿又脏的衣服,才能勉强体面地站在这里,与多慧亲吻。
他不确定,这样的奋力迎合,还能帮他走多远。
但他渴望自己永远适合这里。
所以,他搬起来那块给他全家带来“幸运”的奇石,去结束那几个威胁到他全家永远寄生在这个上流家庭的隐患。
尝过浮华的甜头,便容易生出不甘于此的贪婪。
不是我想带着这块石头,是这块石头死死地粘着我。
是贪婪的念头,扼住了他的意识。
底层的尊严,驱使人类向上仇视。
底层的贪婪,驱使人类向下争夺。
如果贫穷没碰触过富有,它会一直心安理得地待在自己的轨道上。
但是,一旦穷人在豪宅里偷过一夜美梦,若不能及时缓过神来接受自己有可能一辈子都过不上这种日子的残酷现实,那他的手,就可能开始变得血腥。
而这样的心理褶皱,他们却恰恰在指望金钱来熨平。
文|初小轨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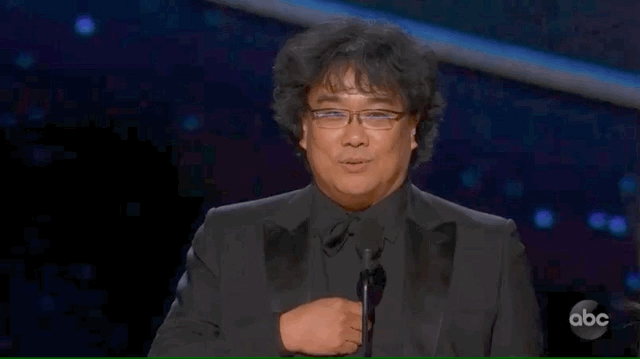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