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讲个故事吧。”小时候总爱要这要那的我们,也都这样恳求过大人。故事能推迟睡觉的时间(或是人类灭绝),而孩子的身体组织还不怎么相信保持苏醒的习惯。它意味着与说故事者之间的关系:听别人说话,这是生活中所有亲密关系的模板。而且,正是在应对故事挑战的过程中,电影由最初一时风行的新鲜事物,发展成了一种全世界共同的娱乐方式,乃至最终成为一门艺术形式。电影始终让我们好奇:讲故事的人有可能会比孩子先睡着,电影却是一种不需要我们在场,自己就能一直延续下去的故事或者说连续性。它就是时间本身,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坚持,时间原本是无须要人来组织的。
放电影是机械的行为,那也是它魅力的一部分,但在这种兴奋之中也含着一丝不祥(没有我们在,电影照样放)。如果一位舞台上的女演员,假设她没法继续演下去了,厄勒克特拉的台词才讲了一半,忽然就停了下来,那么这场表演、这台戏就都停下了。在这种具有其自身动势和持续性的媒介中,这会让故事处在一个有意思但又不确定的位置上。我们的目的是去看,而且很可能让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看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但我们还是会坚持这种想法——给我说个故事,因为故事可以用来避免或者说防止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深渊、失去意义的巨大黑洞,还有因为担心我们没了故事而产生的恐惧感。
想一下2013年的《一切尽失》,雷德福德孤身一人,驾着小艇航行在太平洋上。这是一个很轻松便能呈现出来的故事:它有着一个很突然的开始,而这也差不多意味着,这故事一定要有个解决性的答案。某天早晨,一个年逾古稀的男人独自在小艇里醒来,他距离苏门答腊岛1700英里。之前他感觉到船身猛晃了一下,果然,舱里已灌入了海水。在他睡觉的时候,小艇被集装箱撞了一下,那一定是从某艘货轮上不慎滑落下来的。集装箱呈砖红色,长度可能有六十英尺。它成了深海之中离奇的新怪兽。集装箱里原本装着运动鞋,此刻,它们从因撞击而形成的裂口处随着海水流入太平洋中。小艇损坏得更严重,侧面有条很大的裂缝,只要海浪汹涌,海水就会大量倒灌进来,令小艇很难再浮在水面上。撞击还摧毁了艇上的联络工具(这样的事确实可能发生,尽管在经验丰富的水手看来,这情节太异想天开;不过他被孤立,那是故事需要——那样我们才能接着往下看)。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管这人叫“雷德福德”——他是这部片子里唯一的演员,而且从头至尾的画面里都有他。他并没有一个虚构的名字;影片结束后的演职员表里,他被称作“我们的男人”。这种做法既感人又带着暗示性。它和“我们的英雄”还不太一样,但你也能由此获得一些归属感,而他也因此具有了某种示范性。如果说《一切尽失》是则寓言,“我们的男人”便意味着,他代表了我们所有人。可我们对他还是毫无了解。他是不是正在参加什么单人环球航海比赛?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流行的那种?但我们看不出有这种迹象。他是不是已时日无多,所以正在做最后的自我挑战?他是不是家里遇上了什么无解的窘境,只能用这办法来寻求解脱?他妻子是不是已经去世?还是他为了某个年轻姑娘抛弃了妻子,结果自己又被人蹬了?他是不是有个孩子去世了或是与他脱离了关系?即便你想要探索上述这些可能性,影片也没给出任何线索。我们只是在影片开始时听见他的声音,那时他正在写一条信息,他说自己已竭尽所能——为了这一次能活下来,也为今后继续活下去。我们不清楚这条信息——他会把它装在瓶子里,然后让它漂流出去——究竟是写给他身边亲人的,还是留给所有世人的。“我们的男人”对于我们的存在,我们是谁,都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但如果他是一个故事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故事的听众。我们正在看着他,只有我们离“那儿”很近。
他想用电台呼救,可惜设备受损严重,没能成功,这让他大呼命运的不公。本片由J.C.尚多尔(J.C.Chandor)自编自导,他并未重复内心独白、惊慌失措或精神崩溃的俗套情节。“我们的男人”想要活下来,能想到的办法,他都一一尝试了,但是在他的沉默之中,还是有种默默承受、听天由命的味道。小艇渐渐下沉,他上了救生筏。他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次,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就从他旁边驶过,而且还是大白天,但那艘船上没有瞭望哨,他的呼救未能被人听到。那艘货轮来自一支幽灵舰队,它带着某种不祥,提醒我们别忘了还有另外一艘集装箱货船,正是从它上面落下的红色大家伙撞到了小艇。同时,它还隐喻了那些大企业盲目的动势,他们从不注意亟待援助的个体。
可怕的暴风雨来了,看到“我们的男人”坐在东摇西晃的小艇里被来回折腾,我们依旧相信他能幸存。不过,这场暴风雨完全与大自然无关。虽然摄影机始终在拍摄,我们还是知道,如果演员罗伯特·雷德福德提出要休息一下的话,还是可以获得批准的。夜晚的暴风雨场景,那是在水箱里完成的,波浪也可以人为操控。严苛考验的幻象还是残留下了一部分,但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人为的产物。而且因为“我们的男人”完全孤身一人,这种险情更显得徒有其表。它与那种孤注一掷、命悬一线的故事有许多相似处,但又和证明数学定理时用到的图表一样地直接、理论化。有太多太多的电影里,都有这种“命悬一线”的情境,但几百个工作人员以及一纸完片担保协议都意味着,这一切皆在控制之中。总之,《一切尽失》做到了能让我们相信(与此同时也让我们心有疑窦)。
这时候就体现出片名的重要了。那似乎是在说,早在故事开始之前,结局就已明确,所以常规的悬念理应被摒弃。这片名说的是“我们的男人”和他的小艇,但它更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它是不是甚至有可能指出了21世纪的恐惧,是不是担心我们的文明正以各种各样多到让我们无暇应付的方式趋向于灭亡?在我们观看影片、参与这段磨难的过程中,这个片名似乎已预示了不幸的结局。内心好打听的那一面促使我们自问:“他们”究竟打算怎么结束这部电影?毕竟,故事是由他们起头的,有谁会完全就没想好结局便开始一个故事呢?雷德福德坐上小艇,是不是就是为了寻死?这电影就非得让人看了伤心吗?抑或它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某个能发挥抵消作用的浪漫与感情的源泉,就像是令《泰坦尼克号》大受欢迎的那种力量?“我们的男人”能不能召唤出他的“星期五女郎”来?《一切尽失》不会让人觉得场面上有什么铺张,但它确实由明星主演,故事所涉也都是大场面。据说它的成本只有1000万美元,那意味着雷德福德预先拿到的片酬几乎没多少。但它仍是一部主流电影,一部老式的冒险片,还有机会参加奥斯卡。所以,到底打算怎么结束这个故事,这种悬念从一开始就有。它不可能没完没了地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也不能说停就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号,回家的信号。
我怀疑,J.C.尚多尔曾构思过好几个结局(有朝一日,我们会希望电影里也能看到不同的备用结局,未被采用的故事发展方向都能一一呈现)。让人呼吸急促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这个可以有;或者,救生筏可能会漂流到无人小岛上,“星期五女郎”已为他备好了茶点和同情;甚至还可以让上帝出手干预;影片可以获得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凶猛的助阵;或者我们的男人也有可能会淹死或是因为缺水、暴晒而发疯——这都是人类面对绝境时可能会有的死亡方式;他也可以停止挣扎,投水赴死,就像奥茨船长在1912年从南极回来时离开斯哥特的营地“出去走走”那样。
J.C.尚多尔是一位年轻的美国电影人。在他处女作《利益风暴》(MarginCall)的结尾,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恶心的空虚。在《至暴之年》(AMostViolentYear)里,他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微妙、引人入胜的东西。这一次,他很清楚自己正在拍摄一部罗伯特·雷德福德作品,而且我们关于雷德福德的某种不言自明的假设——不管他演的是什么电影,结尾时他永远都能全身而退,哪怕不一定总能取得胜利——他似乎也很乐于接受。在《虎豹小霸王》(ButchCassidyandtheSundanceKid)里,他即将被射成筛子;在《往日情怀》(TheWayWeWere)里,他选择明哲保身;在《凯德警长》(TheChase)里,他被人谋杀。但他从未被压垮,从未被击败过,他也似乎从没做过堕落、阴险的事。一直以来他都自视甚高——和别的演员一样,他可能也需要这种额外奖励。因此尚多尔设法在保留故事开放性的同时,用一种带有尊严或者说带有尊严的镜像的方式,为影片画上了句号。
那么,对于并非故事理论专家或电影编剧的我们来说,又该如何倾听故事呢?正如希拉里·曼特尔(HilaryMantel)最近所说的,“与其说历史是一种叙述,还不如说它是一组技术。”故事本身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式,它经由电影的重新塑造,变得内涵深奥、令人误解,就像我们对幸福的盲目崇拜一样,故事到了结尾总会皆大欢喜,这个规则屹立不倒。这些主旨直接来源于电影行业的一句古训:如果没法让观众满意而归,他们下一次就不一定还会再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电影里说的故事通常都是积极向上、井然有序的。少了这些忠实的元素,它就有可能让我们看过之后感觉灰心丧气。《公民凯恩》的票房之所以失败(尽管获得的评价很高)是因为它没能按照惯例来满足观众的期待。对“玫瑰花蕾”意义的追寻,几乎完全被遗忘。它只有在你看得足够专注,从头至尾没漏看雪橇,而且对于凯恩的失落感能有所共鸣时,才能产生效果。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发现,凯恩的人生结局并不好,他死的时候并不幸福。死的时候,凯恩已被他自己的那个世界放逐,已被禁锢在他自己的头脑之中,而且影片也未以任何一种常规方式来促使观众关心这个人物。事实上,影片本身对于凯恩的感觉,与绝大多数同事对于奥逊·威尔斯的感觉是一样的,同样暧昧不清。影片如此深入到这个后来成为大亨的小男孩的头脑之中,可结局却来得踯躅犹豫,这让我们感觉不太舒服。
在故事与舒服之间,往往有着紧密关联。“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是一种家长式的承诺,哪怕故事本身有些吓人,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说故事的人会看着你。在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里,浪漫情节中的愚蠢误会,也会以这种方式,在最后一段常规舞蹈与大声喝彩中被扫到一旁。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方式,正在缓缓拉上的大幕上留下了他们最后拥抱的印迹。这也是所有的冒险英雄——从汤姆·米克斯(TomMix,早期西部片巨星)到詹姆斯·邦德,从米老鼠到外星人E.T.——击败仇敌,恢复世界秩序的方式。这不仅是电影里各种叙事元素凑在一起的结果,更是过去三十多年里电视中每天都能找到一打的故事结束方式。仓促,却不会留有余地让人心生怀疑。事情得到了解决,生活回归了平静,就像是出钱赞助这些电视节目的广告片一样地语气肯定、让人安心。哪怕他只是一位衣着寒酸、说话粗俗、相貌平平而且只剩下一只眼睛的警察,科伦坡(Columbo)——或者也可以是佩里·梅森(PerryMason)或《女作家谋杀案》(Murder,SheWrote)里的杰西卡·弗莱彻(JessicaFletcher)——照样能逢案必破,智胜对手。这些正义的捍卫者就和《总统班底》(AllthePresident’sMen)里的鲍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一样值得信赖。那又是罗伯特·雷德福德的一个经典形象,拯救美国免于腐败,坚信报纸能够捍卫宪法。
《总统班底》的成功有它非常巧妙的地方:明星主演、黑色悬疑、对不公正的详细描写,还有保持乐观的信念,相信一切都会变好,报纸也不会消亡。这种乐观主义可以说是美国式的盲目,虽说可能性很小,但在这种盲目背后,更受欢迎的应该还是一次彻底的、批判性的审查。2013年的《修女艾达》(Ida)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一部影片。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波兰,年轻的安娜即将宣誓成为修女,她本以为自己是个孤儿,从小由教会带大。但院长告诉安娜,她其实还有个阿姨,在她迈出宣誓的关键一步之前,必须要去见见这位阿姨。
阿姨旺达对于宗教早已全无信念。作为检察官,有不少人因为她而被处以死刑。但旺达现在已丧失了那份信念,她孤身一人,韶华渐逝,抽烟喝酒样样都来,性生活方面也显得随心所欲、令人失望透顶。她是个怀疑论者,对于自己的事也不想多谈。但对于安娜来说,她有着叙事上的新闻价值——她们都是犹太人,安娜的双亲死于战争年代,凶手是波兰天主教。于是对于艾达来说,旺达此时就像是一道难题:她告诉安娜,你要理解你的过去和你的本质——然后再想想究竟还能不能发誓做修女。毕竟,艾达是你的真名字。
这部影片长度仅80分钟,我不会把结局泄露给你,但我这么说也等于是在承认,这部电影的结局弥足珍贵。对于艾达来说,这注定是一个巨大考验,但同时也成了旺达人生的重要仪式。在此过程中,巨大的罪行渐渐浮出水面,伴之以主人公不得不沮丧接受的一个事实:犯罪者和受害者一样,也都是人。
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结局变得越来越普遍,或者说越来越能赢得尊重。安东尼奥尼的《奇遇》看似讲了一个失踪女子的故事,她在前往离岸荒岛的旅途中人间蒸发。但是很快,对她失踪一事的兴趣便渐渐淡去,与其说是探秘故事,到了最后,它更像是一部有关情感遗忘和不忠的电影。我们始终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了。安东尼奥尼很喜欢这样的结局:《蚀》《放大》,甚至是《过客》(ThePassenger)都在某种停滞中画上了句号。《木兰花》结束得就像是一朵花:那么多的花瓣,有些枯萎,有些盛放。它享受着生命中的野性,所以还包括它的青蛙。《花村》有着英雄式的结局,无能的麦卡比除掉了想要他性命的三个坏蛋,但全镇并无一人看到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会再次遭人误会。在斯科塞斯的《出租汽车司机》里,从根本上就无法适应一切的查韦斯·比克尔,先不论他引发的屠杀,也不论我们对他心智健全的怀疑,事实就是,他仍是这城里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唐人街》里,约翰·休斯顿饰演的诺亚·克洛斯是美国电影里最令人不快的恶棍之一,但他仍控制着洛杉矶,也仍旧是他那个所谓的外孙女(其实是女儿)的监护人。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侦探杰克则在崩溃之际被人带走,留给他的忠告是,“杰克,忘了这事吧,这是唐人街。”——对他来说,这个系统太错综复杂、太腐败堕落了。
电视对于故事的过度摄入,引出了人们带着嘲讽味道的观察结果:在虚构故事的整个历史中,只存在七种或者九种故事形态。观众早已熟悉了这些大同小异的节奏感,故事即便再有创新,观众也不会太拿它当回事。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国家电影院里,有位著名的老观众,每次来看电影时,她都会坐在某一排的最边上,能做到每部电影临近结尾处时,都提前几分钟便退场。她说自己对于电影那套东西早已了如指掌,所以能预感到结局的临近,而且她很讨厌影片末尾那些用来解释剧情的乏味的常规内容。精明的希区柯克就险些被大部分观众对于《精神病患者》结尾的这种解释需要所打败。原本让人不寒而栗的影片,不得不设置了这段让人昏昏欲睡的情节:由西蒙·奥克兰德(SimonOakland)饰演的精神科医生确认我们在散场时,对于片中那奇异的精神病行为能具有必要的认识,心灵得以获得净化。但在此之后,影片还是用我们对于诺曼和他母亲——他们不仅重新聚首,而且互相受到影响——的最后一瞥(和声音),回到了原有轨道上。《精神病患者》用“吓到你了吧”的时刻画上了句号。
此后,对于故事和叙事上一惊一乍的狭隘老旧的强调,让位给了仪式或梦境的再现。在某些当代电影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新的气氛:不再承认生活单纯只是一个故事。生活,更像是一组互相叠盖的故事集合。于是就有了越来越多精选集式的电影(anthologyfilm),例如罗伯特·奥特曼的《纳什维尔》(Nashville)和《人生交叉点》(ShortCuts)、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不羁夜》(BoogieNights)和《木兰花》以及保罗·哈吉斯(PaulHaggis)的《出轨幻想》(ThirdPerson)。相对于我们平时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这类电影似乎来得更为真实,而且它们注意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一种体会:他或她感觉到,自己一定是宇宙的中心,是一颗星,其实我们却只是一个个被别人包围着的电影配角。
在故事里,我们心系人物的道德主体。这是19世纪时各种语言的小说都具有的关键所在,之后它又延续到了电影之中,至少有一百年时间。所以我们会关心郝思嘉的命运,还有《郎心似铁》里的蒙哥马利·克里福特(MontgomeryClift)、《正午》中的威尔·凯恩警长以及《彗星美人》里的贝蒂·戴维斯和安娜·巴克斯特(AnneBaxter)。剧中人为正义而战,克服艰难险阻,寻得自我,获得真爱;这看似是电影里一种正统的做法。但在这千篇一律的风景里,也有着野性十足的地带。1944年的《江湖侠侣》和1946年的《长眠不醒》,都对战争年代的动作类型片和侦探故事加以轻蔑、漫不经心的嘲弄,两部影片完全成为鲍嘉和白考尔随性而至的作品。但他们俩或许当时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是导演霍华德·霍克斯自己,可能也不太确定。只是,事实就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类型的电影,那是针对电影里固定习俗的嘲讽。类似这样的做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再也无人敢于问津,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戈达尔那些作品的出现。那些作品都是些针对好莱坞体系随性、美好却又充满嘲弄的翻拍片。
但时代在变,热衷于思考该如何看电影的人,如今常追的却是被我们称作长篇电视剧的东西,那是由特定情境和人物构成的系列版本,有可能一播就是好几季。这些剧集的制作预算和拍摄计划,都可以追溯到好莱坞的工厂体制。它们倚重的是优秀的剧作和良好的角色演出,它们比较喜欢聚焦于一群必须面对戏剧性危机却又没法很好地处理危机的人物。整部剧集也可能因此而结束。我此刻想到了《黑道家族》、《火线》、《国土安全》、《大爱》(BigLove)、《演播时刻》(TheHour)、《堕落》(TheFall)、《无路可退》(Rubicon)、《鸿运赛马》(Luck)、《性爱大师》(MastersofSex)、《清道夫》(RayDonovan)、《大西洋帝国》(BoardwalkEmpire)、《绝命毒师》和《浴血黑帮》(PeakyBlinders)等剧集。其中有一些,相比另外一些要更成功一些,或者说活下来更久一些。但那种成功也表现出一些创作上的问题来。
《国土安全》开播于2011年,由阿莱克斯·甘萨(AlexGansa)与霍华德·哥顿(HowardGordon)担任主创(剧集由一套以色列连续剧衍生而来)。支撑这出剧的是凯莉·马西森这个人物,她是一位出色的中情局特工,但也患有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需要定期接受治疗,即便这样她也频频濒临精神崩溃。第一季中,她与达米安·刘易斯(DamianLewis)饰演的布罗迪有了联系,布罗迪是从伊拉克归来的战俘,有可能已成了恐怖分子。凯莉必须要对他仔细调查,她却在此过程中爱上了他。这样的设置,一下子就夸大了剧情的可信度。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中情局应该不太会愿意雇佣一名爱上了行动目标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患者。同样,遭受如此怀疑的布罗迪竟会加入总统选举团队,还得到了副总统提名,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即便如此,第一季还是在间谍悬疑与备受折磨的爱情戏中达到了高潮,而凯莉则被送入医院,接受休克疗法。克莱尔·丹尼斯(ClaireDanes)在该剧中的演出,在同一时期的影视作品中,无人能出其右。她确实非常出色,甚至克服了大众对缺乏可信度的担心。她获得各种奖项,通过她的演出,我们中的许多人第一次见识了被诠释得如此出色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状况。这和看着真正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病人受痛苦折磨是两回事。
之后就是第二季了,发生的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但悬而未决的信任危机,相比第一季来说是更大的考验。
然后是第三季,这一次……幕后创作团队(克莱尔·丹尼斯此时也已成了该剧制片人之一)似乎意识到了,那些让人难以相信的情景已距离瞎胡闹仅仅一步之遥了。于是曼迪·帕廷金(MandyPatinkin)饰演的中情局行动主管索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指责凯莉,承认她情绪不稳定、不可靠。她被解职,送返医院。有一集中,她艰难的康复生活,与布罗迪在南美洲某国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情节平行推进。此后,《国土安全》的真相浮出了水面:现在的凯莉是假装自己仍患有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但她也已快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这些都是她和索尔策划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引诱伊朗情报部门上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女演员在剧中扮演一位女演员。
发生在《国土安全》身上的事情就是,为了满足商业胃口而让故事做了牺牲(有点像是调整球赛开场时间以适应整个电视播出计划)。情节上的转折为之后的故事挖下了更大的坑。在第三季中,布罗迪被处决,凯莉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接下来呢?第四季想要加紧在海外阴谋与悬念上做文章,于是凯莉会被送去伊斯坦布尔或是巴基斯坦的某个岗位。可她的孩子能一起去吗?我想,编剧一定是觉得小孩子只能碍事(此时布罗迪的家庭早已被完全抛弃了),所以她被留在了家里,由凯莉的姐姐负责照顾。
这也让我到了极限(这让我更清楚地体会到了当初大卫·切斯以某种意味深长的空白给《黑道家族》画上句号时所体现出的嘲弄人的微妙感觉)。一个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患者能得到中情局的特别信任,这我能看得下去;她和一个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男人爱得火热,这我也还能看得下去:侦探就是会瞎搞嘛。而且我喜欢克莱尔·丹尼斯赋予这个角色的不加掩饰的人性。但是,当她的小孩都被丢下时,我弃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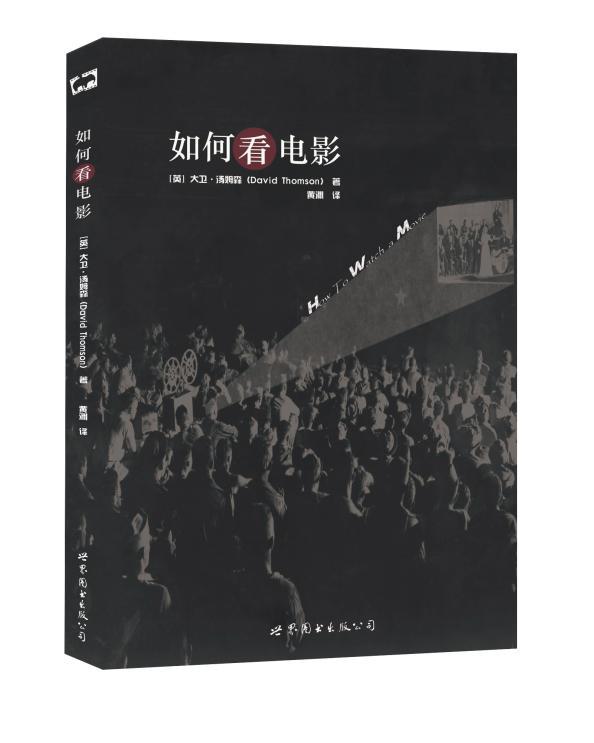
作者:[英]大卫·汤姆森(DavidThomson)
译者:黄渊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书号:978-7-5192-1923-9
出版时间: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