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今年的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回顾这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民族复兴路上,在她的领导下,举国上下赢得了新冠疫情的阶段性胜利。期间中华民族从个人到集体都体现了处危不惊,逆势奋进、万众一心的精神。这种不凡的气质,其根源可在庞朴先生的这篇《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中找到相关答案,同样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需要这种精神。以此文与广大读者共勉。因篇幅关系,有关忧乐文化如何塑造民族性格,以及对两种学说的进一步精彩阐释和不同见解,可参见新著,从中也可感受庞朴先生扎实的功力、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对现实的关怀。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庞朴著、冯建国编,责任编辑:储德天,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6月,定价68元
【正文摘编】
对中华文化特质的界定上,有无数观点。徐复观先生的“忧患意识”与李泽厚先生的“乐感文化”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圈子里,都发生了强烈影响。
分析这一对都已颇具影响的学说对于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课题,岂不也算在尽一点绵力么? !
徐复观提出忧患意识:人具备自我主体性后的自我把握和升进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
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与绝望气氛中,总是感到人类过分渺小,一凭外在的神鬼为自己作决定,因而人的行动脱离了自己意志主动或理智导引,没有道德可言。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取词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某种欲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与形成耶、佛二教的 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绝然不同。
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 则融入于“礼”,尔后更升进为“仁”。从表面看来,人是通过“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质地说,实乃天命、天道通过“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作为人的本体,成为人的“真实的主体性”。 他们相信,基于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 化了以后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

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左起: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
李泽厚提出“乐感文化”:实践理性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原型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而这一说法的理论前提,早在他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中,便已形成了。
其说认为,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及长期延续, 以及以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 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 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由文化转变来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虽历经阶级的分野与时代的变迁,它却保有其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实用理性引导人们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执着态度,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在消灭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灵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于抽象思辨的概念体系中探索无限的奥秘;而只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在人世快乐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无限。
这种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是知与行统一、体与用不二、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表现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乐感文化。据说这个所谓“乐”,还不只是心理的情感原则,而且是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在中国哲学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是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是巨大深厚无可抵挡的乐观力量,是人的心理本体,那个最后的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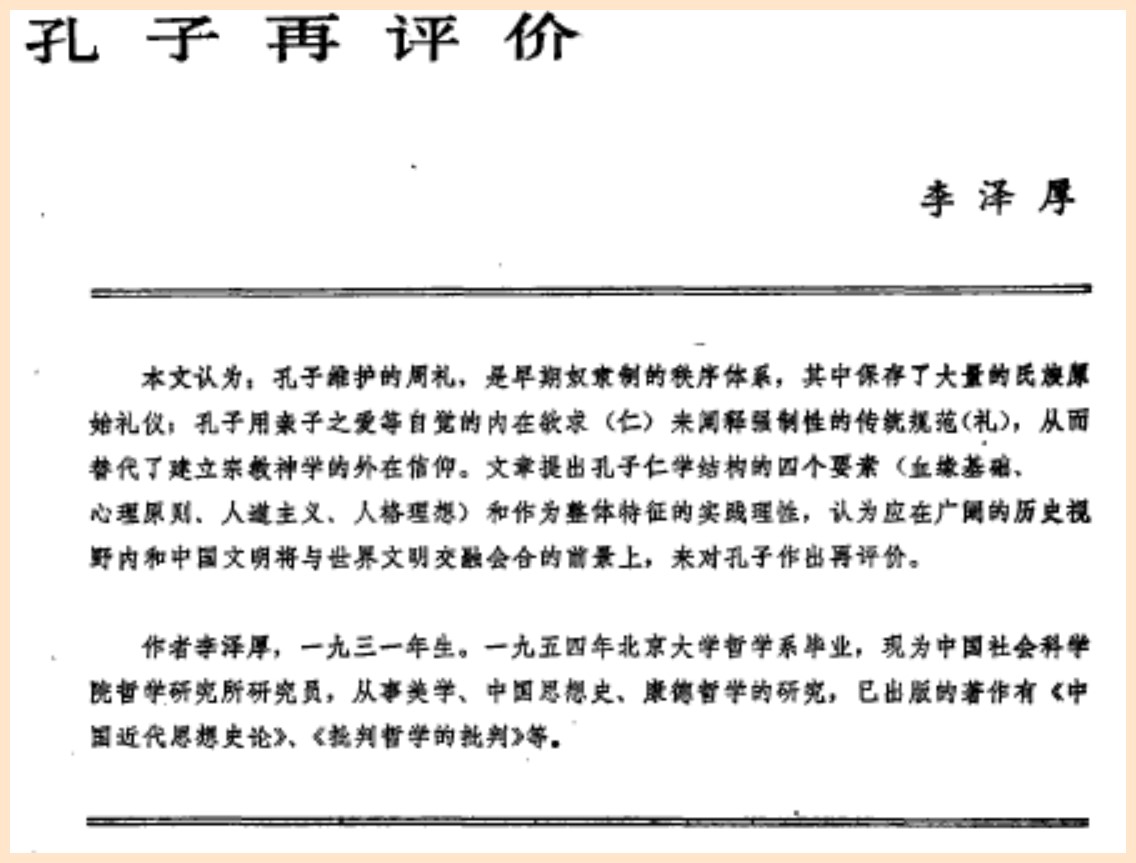
李泽厚在1980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形成了“乐感文化”的理论前提
忧乐共同处:认同儒家为根基的民族文化,都追求天人合一
乍一看去,以“忧”“乐”二义统领中国文化,其势当如水火,绝无相容余地。但稍加寻绎,却可看出,两说偏又颇多共同之处。
首先,二者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今天和过去之间构建某种理想的承续关系,以度过时代冲击的震荡,为自己的灵魂和民族的命运定立方位。
第二,二者都以儒家思想为母体,由之引出一个原则,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化的属性。
第三,“忧”“乐”二说都强调中国文化之非宗教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证明它的人文性。“忧”说区分恐怖意识与忧患意识在心理上的不同,证明二者分别造就了国外的否定人生的种种宗教与中国的肯定人生的人文文化;“乐”说则从实用理性与思辨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区别着手,证明中国人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国,虽幻想成仙或求神拜佛,都还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与快乐。
当然否认中国文化为宗教不等于否认它具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境界,二说都极力证明这种超越的存在。“忧”说认为,天命或天道是超越的, 天降命于人或天道贯注于人身时,又内在于人而成为人性,使人有道德属性。人通过基于忧患意识而起的道德实践即尽人之性,便可以领悟到天命或天道的存在,体验到道德自我(不同于生理的、心理的乃至思考的自我)的存在,而到达超越的境界。这便是性与天命的贯通,天与人的合一。
与这种降命和尽性不同,“乐”说更重视审美的直觉。它认为,超越、无限之类在当下的现实和人际关系之中,在“工商耕稼”“伦常日用”之中,甚至就是“伦常日用”本身。而由于宇宙本体也被认定为乐的(“生生”“天行健”),于是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即是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在追求天人合一上,“忧”“乐”二说又殊途同归了。

庞朴在其自选集《三生万物》的自序中评价自己是“非僧非道一醉翁”
忧乐相异:忧患意识具有道德价值,乐感文化强调审美境界
当然,“忧”“乐”二说相互不同之处,比起它们的相同来,要更加明显而且重要。
首先,“忧患意识”说所欲寻求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这个动力不仅是“能”,更且被视为“质”,所以“忧患意识”有时也被说成是人类精神,或者叫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悲悯之情,一种宇宙的悲情。
“乐感文化” 说所要探讨的是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曰民族性、国民性。更精确点说,是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心理结构,是人格化了的文化传统,或民族的文化性格。成形于孔子与儒家的塑造,作用于悠久的历史,并在今天的现实中存在。研究它在适应现代生活中的不足和裕如,将有助于改进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智慧,有助于主动去创造历史。
其次,“忧患意识”的内涵不管怎样界定,总之它是一种“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又不只是对忧患的知觉或他觉,而是知其为忧患遂因应生起来一种意志,或当前虽无忧患存在亦能存有此种意志(居安思危)的那样一种觉识。忧患意识其实乃是对于仁心或善性的某种自觉。因而,忧患意识只能是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意识。苏东坡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开卷惝恍令人愁”。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乐感文化”所表示的文化心理结构,据作者说,是全民族性的,它是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它便不止于为民族的某些人例如知识精英所专有,而是普存于民族的每一成员心理之中。所谓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有人简化为“种族记忆”。
它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它不是精英们的自觉,而不过是种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罢了。
第三,“忧患意识”说认为忧患意识本身已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且能引申出种种道德信念来,而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重道德性的总根源。换句话说,美与真,如未通过善之自觉认可,仍不过是些浮游无根、飘忽不定之灵气而已,唯善为大,是它赋予了生活和世界以和谐、秩序、真实。
“乐感文化”说则超越诸如此类的道德灵光,更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和宇宙。它认为,中国人更惯于快慰地把握现在,乐观地眺望未来,在感性生活中积淀着理性精神,于人生快乐中获得神志超越。因而,审美境界是中国人生的最高境界,审美主题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最高标的。而“乐感”,这一为审美所必备的心态,则是中国人的心理本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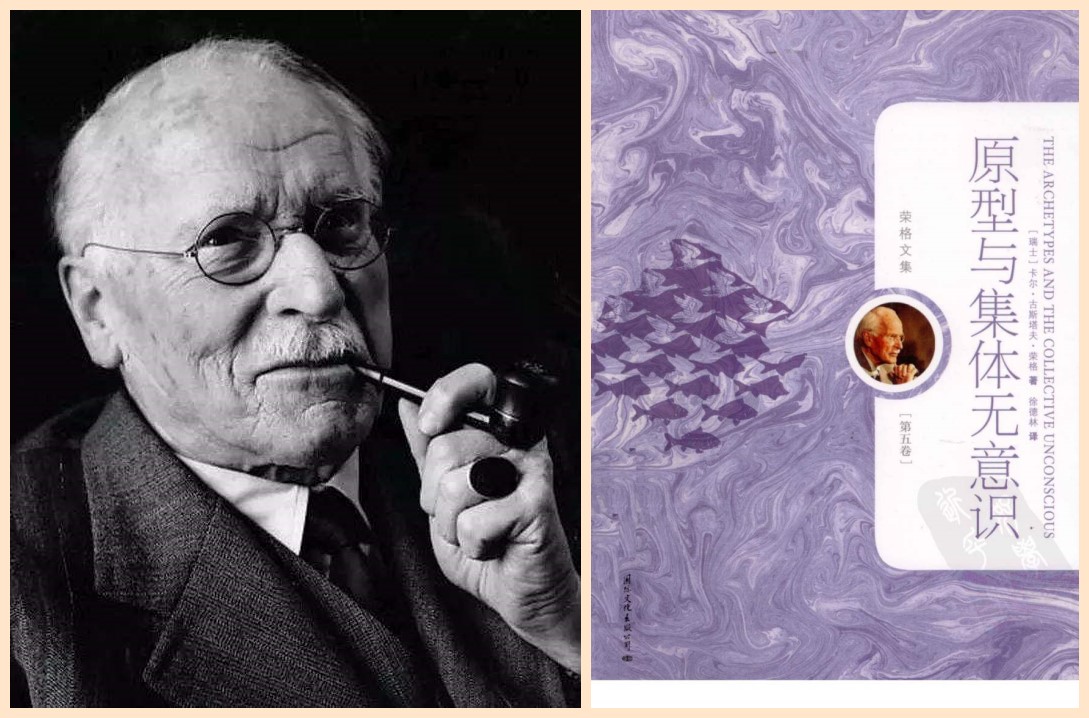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1875-1961)提出“集体无意识”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
中国文化兼备忧乐精神,形成中国的理想人格,极具辩证法
经过西汉以来儒道的争辩,人们在习惯上便以庄子的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乐观的代表;而儒家的乐感既流入道家去发扬光大,剩下的忧患意识,便特别引人注目了。自此,儒道两家思想轮番地、混合地、谐和地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后来更熔化了外来的佛学于一炉,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新的统一体。而其精神,或可即以“忧乐”二字给以概括。
所谓“忧”,展现为如临如履、奋发图强、致君尧舜、取义成仁之类的积极入世态度;而所谓“乐”,则包含有啜菽饮水、白首松云、虚与委蛇、遂性率真之类的逍遥自得情怀。
以上种种忧乐杂陈的状况,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完整的性格,或人们的个性常是双重的、分裂的;相反,它们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即由儒家思想流传下来的忧患精神和由道家思想流传下来的怡乐精神。
这两种精神的理想结合,便构成了中国人的理想的人格。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朱光潜),两千多年来的人格设计方案,大都如此。而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入浅出的,大概要推孔子的自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第一句“发愤忘食”是忧,第二句“乐以忘忧”是乐;至于这第三句,既可以说是由“忘食”而引发来忘年的伏枥之志,也可以说是由“忘忧”而不觉岁月匆匆之自得之情;或者,此志此情已浑成一心,可以从其所欲而无往不适。此志乃修德所养,亦得道表现,因而忧即是乐;而此情乃得道之貌,即修德结果,因而乐即是忧。如果再进一步推敲,“不知老之将至”中,还有从忘食忘忧而到达忘我的意思,那么在此境界中,便又无忧无乐可言,进入“高峰体验”之 中,自己与世界同一而无特定情感了。
孔子的自白经孟子的条理化后,形成了人格规范。孟子认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虽都是圣人之行,却都不及孔子能集三人之大成,而成为“圣之时者”。所谓“时”,是进退、出处、远近、迟速,都能因其所宜而为之,不拘于一曲,不名于一德,圣而不可知之之谓。这是统摄忧乐而又超越忧乐的境界。
孟子归纳的这一人格系列,充分显现了中国式辩证法的神采。它不同于古希腊辩证法的两极对峙,也有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正反加合;它不是来自对自然界以及对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静态直观,而是建基于对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现象——人文现象的透辟理解。因而,它能更全面、更深刻、更细腻地反映着客观法则,为人的智慧升华架设了天梯。

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中对古代四位大圣贤进行过境界大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孔子第一,伊尹第二,柳下惠第三,伯夷居末
圆融的优势使外来文化融入、内化,并汇成忧乐圆融的东方人文精神
正由于中国文化中不乏此种精到的辩证传统,所以后来佛学传来的某些纯思辨东西,便不难被吸纳被融化了。佛学有所谓四门诀——无门、有门、亦有亦无门、非有非无门,与孟子的四圣、庄子的四相,完全是一个套子。天台宗的中观于“假”(实际)、“空”(真际)之外,将“中”分为“隔历之中”与“圆融之中”,或“但中”与“不但中”。其隔历之中(但中)谓中在有无或假空之外,绝待而有;圆融之中(不但中)谓假空中本一法之异名,即假即空即中。这两种“中”的不同,也就是孟子的“和”与“时”的不同,庄子的“太冲莫朕”与“环中”的不同。 而所谓假与空,则不过是“任”与“清”、“天壤”与“地文”的佛学说法而已。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化约为阴和阳或忧和乐,归之于阴阳的统一和忧乐的圆融。
圆融既被推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人格的最高境界,于是两家虽仍存有偏忧偏乐的差异乃至对立,恰正好成了检验他们的学说能否贯彻到底和考验他们的人格能否臻于至上的试金之石。所以,他们走了“仇必和而解”的光明大道,互相圆融起来建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而将偏至旁行者及其彼此的坚决斗争到底视为末流了。
圆融也成为一种优势,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因它的迷狂和辨析而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论证和充实,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的、雄峙东方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这是一种“精神”,不同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精神是受到称道和景仰的集体意识,它代表着这个集体并培育着这个集体,凝聚着这个集体也传承着这个集体。它不是先验的,既不先于这个集体的经验而为人的本性或天道所固有,也不先于每个个人经验而由这个集体的族类所积淀。它源于生活并塑造着生活,来自历史也构成着历史,保存在传统文化之中并流衍而为文化传统。它既有内容也有形式,既有结构也发生功能,既受精英所仰止也为百姓所追求,并且达到圆融的状态。
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变化是不大的。时至今日,它正迎接着新的挑战。我们相信,正是圆融本身,可以促使它不泥于一曲,不止于故步,不扬彼抑此,不 厚古薄今;可以保证它取长补短而不崇洋媚外,革故鼎新而不妄自菲薄,适应时代而不数典忘祖,认同自己而不唯我独尊。
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我们正在发扬这种精神。
(李念摘编于《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第二编同名文章,原文1.8万字。原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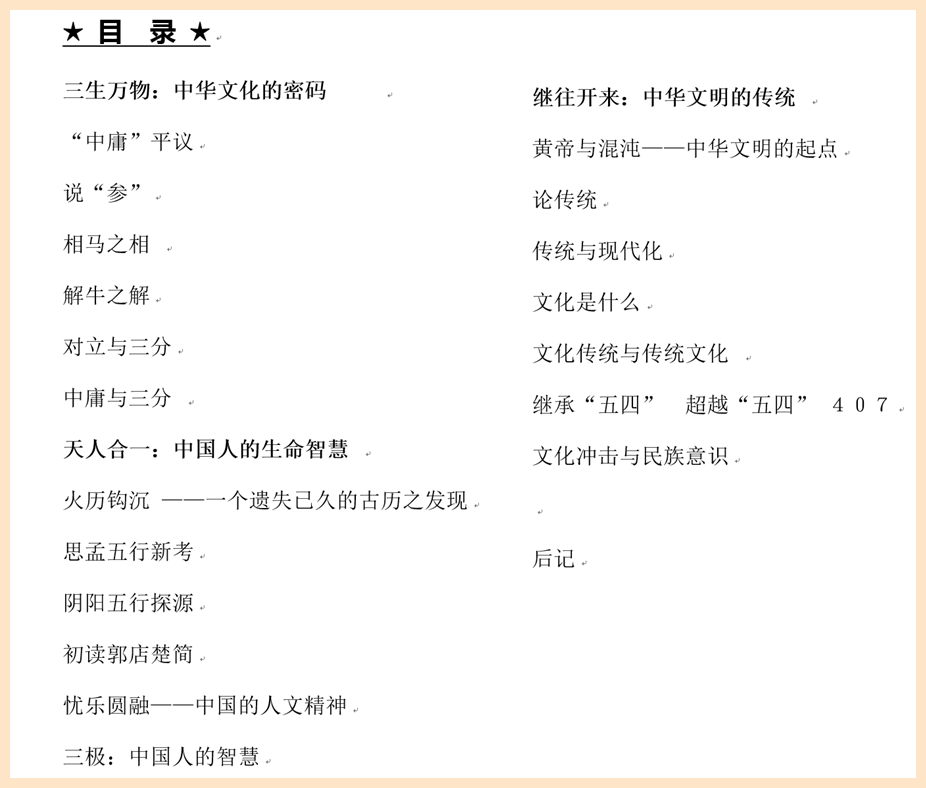
作者:庞朴
编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