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金庸和古龙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他们都是一流的、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不能说金庸这种写法就一定好,古龙这种写法就一定不好,同样是金庸的这种写法,换了别的作家,他可能就写得不好。今天许许多多人,也有模仿金庸的,也有模仿古龙的,但都模仿得不到家。
外貌描写
人到底可不可以貌相?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果人真的不可貌相,那文学作品中为什么用那么大篇幅写人的外貌呢?为什么演戏剧作品还要画脸谱?所以我想“人不可貌相”好像不全面,好像有问题。那我们再看看,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人不可貌相”的?“人不可貌相”其实是说人不可简单地“貌相”—你不要认为人长得漂亮就是好人,长得不漂亮就是坏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是管用的。
我们知道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高人就会看相。这里的看相不是看相面那种看——“我料定你二十五岁必有一劫”(众笑),不是这样看相。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他有各种生存活动,这种活动会在他的表情上、身体上、外表上留下烙印。我们经常看到这些烙印,根据这些烙印我们就对这个人的命运、性格,有了某种积累下来的经验,经验多了就可能变成一种直觉。专家可能会去总结长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性格,这是专家总结。我们一般人没有总结,我们根据经验,会发现这个人长得挺面善的,这人挺和蔼,那人长得特别阴森。我们看中国历史著作中描写人也经常描写外貌,描写外貌重点不是让人记住他的带相片性质的特征,这个外貌说的都是人的性格。
比如描写某个大臣“鹰视狼顾”,哎,这个人性格已经出来了:很厉害,很阴,很多疑,很狡诈。你在后面跟着他走,突然他像狼一样回头看你一眼,“鹰视狼顾”。说明人是可以貌相的。我是很多很多年前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努力地去以貌相人,但是我不告诉别人我怎么相的。我很自豪的一点是我看人比较准确,当然不仅仅是通过貌,还通过语言,通过肢体语言,我还看了一些心理学著作,所以我跟人打交道,上当率比较低。我看人的功夫相当于小李飞刀,他还在那儿坐在我面前继续骗我呢,我心里一把刀已经“插”到他“咽喉”上了(众笑)。
人其实可以貌相,正因为人可以貌相,文学家才利用这一点影响读者对这个人物的观感。作家描写人不是在那里给他照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小说家写人的时候,一个人物出场,后面配个照片多好。这样肯定就砸了,这样就不是小说了。为什么大多数电视剧不讨人喜欢呢,就因为那个人是活的,让我们看见他长什么样了,一看见长什么样,文学性就没有了,在此时此刻退场了。特别是你读过优秀的文学名著之后,你特别怕它被拍成影视作品。如果拍成影视作品后,你看到这人跟你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一致的时候你还比较欣慰,多数情况下并不一致。也许先看了影视作品,后看原著,比较好。

那比较之下,金庸的外貌描写,他主要写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主要写的是这个人的气质。我们看人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气质,中国人评价人都是用气质来评价,说那个人长得阴嗖嗖的,这个东西很难说,很难量化,很难定性。文学家就是利用这个道理来影响读者对一个人的观感。正因为这样,金庸喜欢写人的眼睛。
金庸喜欢写人的眼睛,不是说每个人物他都写眼睛了,而是从比例上说他不自觉地重视写人的眼睛。金庸不承认自己受五四文学影响,他不承认是不管用的,只有中国新文学几十年发展积累下来中国人整个的文学经验,到了金庸这里他才写得这么好。重视写眼睛的问题鲁迅早就说过了,鲁迅写人最重要的就是写眼睛,写眼神、写眼光,你再看看茅盾、老舍和郭沫若等都是这样,都重视写眼睛,写眼睛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眼睛是非常难写的,写眼睛不是说这个人是三角眼,这个人是丹凤眼,不是这个意思,这留不下印象。你好好看看鲁迅和金庸,他们是怎么写人的眼睛的。
演戏也是这样,真正好的演员练的都是眼神,你看戏曲舞台上讲手、眼、身、法、步,俞振飞先生回忆他跟梅兰芳同台演戏,两人都演了多少回了,他说上台后梅兰芳一眼看过来,他浑身都酥了(众笑)。你想他俩都是男的啊,梅兰芳是男扮女装,所以说梅先生这眼神太厉害了,一扫过来俞振飞就不行了(众笑)。这就是说戏曲演员眼神的厉害。那我们想想文学家为什么重视写眼睛?眼睛就是灵魂,通过眼睛能写出这个人物来。

齐白石与梅兰芳
古龙很喜欢写人的衣服,这一点其实也可以挖掘,古龙为什么喜欢写人的衣服?第一他很重视衣服,他很重视穿什么,这是作家物质生活的一个折射。另外呢,衣服是跟身体挨在一起的,他很重视身体,我们看古龙小说中有大量的身体描写,特别是对女性身体的描写。那也有人说这么写不是更现代吗?从某个角度说是更现代,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就像我们刚才解释衣服一样,这两个东西对他来说都不容易获得。我们不了解古龙这人,看小说就能看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武功描写
武功描写,是古龙、金庸差别最大的地方。外貌描写两个人还有很多相同之处。古龙的小说省略中间过程——这刀一飞出去就得死,这我们大家都熟悉了。那么它说明什么问题呢?读金庸的小说你可以发现,他随随便便用几百字写两人打架那太常见了,用千八百字、几千字写一场打架也很常见。一场大战写一章两章,中间无数的人对打乱打,那场面极其浩瀚。那么这里面涉及一个叙事时间的问题。你看刚才戴同学举的黄蓉打李莫愁的例子,其实是电光石火之间发生的事情,可是你读那段文字,恐怕要读好几分钟,你读的是作者给你设置的在叙事时间里的活动,而黄蓉和李莫愁或者别人也好,他们在故事里度过的是另一个时间段。用我们的专业表述叫“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以后你读小说有闲工夫的时候看一看,小说里哪些部分叙事时间等于故事时间,哪些部分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哪些是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它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从头到尾一共写了多少年间的事,一共多少章,然后你看看其中用最大的篇幅写的是哪几年。主要的篇幅都是写“赤壁之战”那段了,然后其他事情过得飞快,后头过得特别快。

武打也是这样,主要时间用在哪儿?本来二十秒(故事时间)就结束的事,你看金庸写的,两个人打得那么漂亮。你去读,读了半天,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获得了审美享受呢?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时候,为什么你就获得美感或者快感了呢?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时间改变了,你等于把“人生流”切断,进去了,你的生命进到一个隐秘的时空里,那个时空单独为你放慢了它的节奏。那个时空本来是二十秒,但是为了你变成了两分钟,变成了五分钟。如果你高兴,那还可以再重读一遍〔众笑〕。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你看,你还可以重复。所以人在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时候,仿佛生命得到了延长。这是金庸这种写法的一个特点。但是,是不是叙事时间比故事时间越长越好?长到什么程度好?因为时间是可以无限切割的,可以无限延长。比如我们一个同学喜欢睡懒觉,早上舍友叫他起来:“上课了,快起床!”他说:“你给我数到10我就起。”“好,1、2、3、4、5、6、7、8、9......”他说:“我接着数,9.1、9.2、9.3......”他数到9.9,还可以数9.91,时间是可以无限切割的,切割到什么程度好?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武打过程,金庸、古龙两个人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从金庸和古龙的不同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追求的是不一样的,金庸的武打让人享受这个过程,而古龙的武打呢,你看出他很着急,他追求结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分析一下什么人喜欢金庸,什么人喜欢古龙,还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去分析,他什么时候喜欢金庸,什么时候喜欢古龙。你看金庸这种写法和古龙这套写法的不同,不仅仅说明一个人不缺钱,不着急要稿费,另一个人特缺钱,要“骗”稿费,这还是比较表层的原因。
它有一种深层的东西,你读金庸的小说你会觉得背后的叙述者,他对世界充满了自信,他不着急,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永远写下去,就看他愿意不愿意。这个世界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想让谁胜就让谁胜,都不影响小说的精彩。他慢慢地欣赏过程,就像我听说过的,希腊山崖上刻着的一句话:“慢慢地走,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金庸的小说就是让你一路欣赏的,按理说这是一种很成功的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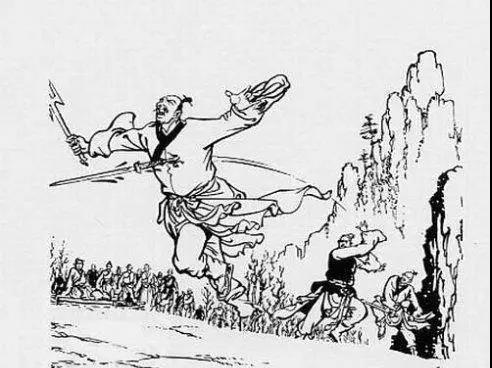
可是古龙好像就比较着急,古龙要直奔结果,尽管前边做了很多的铺垫。按理说如果像金庸、梁羽生这样的作家做了很多铺垫,一旦开打,会更精彩。就像我小的时候看电影,一般前边有一段加演片(小时候没有电视,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前面有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别的小电影、新闻联播,或者一小部动画片,什么《小蝌蚪找妈妈》这些)。前边的东西演得越多,我知道后边电影越棒、越精彩。如果前边加演片演完了,“啪”灯一亮,换场了,那大家肯定会愤怒了。古龙就经常这样,这前边铺垫得很精彩,然后突然就结束了。从这里能够感到作者对生活的一种恐惧。他表现得特阳刚、特自信、特牛、特帅,其实他恐惧,他不敢生活,他对生活早就失去勇气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一篇文章叫《生活的勇气》,也是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写的是我去看契诃夫的一出戏。有的人生活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生活,他太讨厌这个生活了,他不论怎么表现,寻欢作乐也好,刻苦上进也好,其实他骨子里是害怕生活的,每一天他都发愁。他像出租车司机一样,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欠人家几百块钱,这一天大半时间要为着“份儿钱”而奋战,从早上起来开车开到下午四点,这钱是给别人挣的,四点钟以后的钱才是自己的,每天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是烦的,是烦躁的。我们读古龙的小说就可以感到他挺烦,这个人不喜欢生活,所以他经常要把生活写得很刺激,充满了美女、美酒,特别夸张的美好的东西,夸张的享受、夸张的刺激,他特别愿意刻画鲜血。古龙的小说里有明显的嗜血的成分,特别爱写这一剑刺到咽喉上,“啪”一朵鲜红的花开了。有很多学者批评古龙,说这样写不好,说这样写“残暴、血腥”等。我看到的是古龙的一颗受伤的心。古龙是一个缺少温暖的、缺少爱的人,他真的是一个浪子。假如我遇见古龙,我一定请他大吃一顿,最后给他一笔钱。因为我能够看清楚这种哥们儿,他其实内心里很善良,然后装得特倔,装得很残暴,因为他对生活的感知,不敢直接表露出来,但是我们分析小说的人,就能分析出来。
而金庸呢,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是个成功者,不断成功,尽管他的成功也不容易,有过风浪有过挫折,但是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乐趣,他是这种豪迈的大英雄。所以金庸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可敬,读金庸越读越佩服,说这老爷子太厉害了。而古龙真正让人怜爱。你会发现你们班里什么人喜欢古龙,就是自己有点浪子情结的,不喜欢考试的,其实是惧怕考试的,然后疯狂地咒骂我们的体制不好,其实是自己没本事,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喜欢古龙。

有的人一读金庸就有点烦:“怎么还有,怎么还没有打完呢!”我们觉得金庸写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好好看呢?他着急,他不看这些,他要看结果,他要看谁把谁打赢了,也就是说他不敢生活,不敢进入那个过程,不敢享受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而古龙有时候是反过来,古龙有时候是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可能实际上打了十分钟,他两行就结束战斗了。他这么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不就是想出家的一种心态吗?其实就是厌世心理。所以古龙的创作和他本人的生活一道,都是对他所身处的社会的控诉和批判。他自己被出版商剥削,被各界利用,虽然有很多读者,这些读者真的理解他吗?不一定理解他。所以我们看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很狠、无情,很残暴,让他们受苦、流血、被蹂躏,让他们发疯,而且没有来由地发疯。他随便改变自己小说的情节进展,他自己的人物经常出来说话,他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可以说“人本来就是常常要发疯的”(众笑),他小说怎么写怎么有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古龙到底能不能在新武侠界排进前三名、前五名、前十名,看怎么比。正因为他这一面太突出了,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了,所以才存在着拿金庸和古龙比这一现象。其实更好跟古龙比的对象是梁羽生,因为金庸有些东西还能覆盖住古龙,他和古龙不是完全两极对立的,跟古龙真正对立,可以最好比较的是梁羽生。因为梁羽生特正、特稳健,古龙是特别邪,金庸的小说是覆盖在他们二人之上的,另一种层次的功夫。
性格描写
最后说性格描写。就像在金庸的小说中找不着“金庸侠语”,找不着名人警句一样,直接写一个人是什么性格这是文学描写的大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古龙不但没上过什么学,没有学过文艺理论,可能真正的文学作品读得也不太多,或者也许读过,但是是囫囵吞枣乱读的。真正读得好的话就知道不能直接说人是什么性格,尽量要删掉。前代武侠小说作家白羽,年轻时曾经算是鲁迅的学生,向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请教文学创作方法,把自己写的作品拿给鲁迅来修改。鲁迅看了之后说,你这小说写得不错,给你改一个地方,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说“可怜这个老人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了”。鲁迅说把“可怜”给你改了,改成“可是”。真正聪明的学生,老师给你改一个字你就受益终生,就明白了。白羽就明白了,写“可怜”等于作者的态度已经表露出来了。这个老人到底可怜不可怜,由读者自行去感觉,若读者没有感觉到,你强加给他,你说是“可怜”,没有用,他记不住,他自己悟出来的才有用。所以,鲁迅他是现实主义描写的大师,鲁迅的作品里面就没有这些词。我们都学过,比如《孔乙己》,鲁迅说过“孔乙己是多么可怜啊”,说过吗?没有。但里面写的都是大家怎么糟蹋他,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孔乙己可怜。鲁迅这样的作家绝不会喊:“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啊!看这些吃人的家伙!”从来没有这种话。
那么,金庸不会承认他受鲁迅影响,受“五四”影响,他不会承认他受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影响,但是金庸的作品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最佳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文艺的时候就说过,作品的倾向性要随着情节的描写自然流露出来。每个作家都是有倾向性的,只不过表达倾向性的手法不一样。好的作家的倾向性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你不要像写作文一样,自己去下断语,自己把观点推出来,作品不是论文。恩格斯说最忌讳就是传声筒,人物成了你思想的传声筒,你唯恐读者不明白,自己抢着说“这个坏人”,千万不能这样。

但是,我们要考虑这是一种理想状况,这是一种提升的文学,让人们不断有修养的文学。而事实是社会上大量的人他没有那个耐心,也没有那个修养,就希望知道结果,就希望能够简单地以貌取人、不动脑筋,你得告诉他这人是好人坏人。特别是我们童年时期,都是在听童话寓言中长大的,大人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习惯于这种模式—这是好人,这是坏蛋。然后,这个孩子如果不能提高,不能摆脱这种模式,我们看文学作品就习惯了——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习惯于这样。很多人都习惯于这样看文学作品,要把人物脸谱化、模式化。金庸不命名他笔下的人物的性格,结果我们至少都能记住他笔下几十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水平比较高的“金迷”能记住数以百计的金庸笔下的人,金庸能说一个,活一个,这些人在脑海中都是活生生的。这些人之所以是活生生的,是因为你不容易概括他的性格,哪怕是我们大家都再有共识的一个人,也很难用一套共同的词把他说死了。你说黄蓉是什么性格?大家说出来其实是不一样的,说出来不一样,她才是一个活的人。
而古龙按照他的描写路子,就已经算最成功了。这种路子,是脸谱化的描写、符号化的描写,唯恐我们记不住,他事先把标准答案都写在那里,可是恰恰因为写了标准答案,效果不理想。我们记住了很多古龙笔下的人的名字,其实那些形象反而是模糊的。很多名字之间有大量的重复,李寻欢、荆无命和叶开,这些人你想多了之后,发现重复率极高。所以,古龙的小说也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文学的一个绝佳样板。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没有读武侠小说,上《文学概论》课的时候,老师就说文学作品不能这么写,但是你让他举个例子他又举不出来,因为这样写的书没有留下来,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我看了古龙的书明白了,这不就是反面教材吗〔众笑〕?文学作品不能这么写。
那么,这种例子不仅在武侠小说中有,我小的时候读了大量的革命题材的作品,发现很多革命作家也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呢?我们很多革命作家文化水平不高,他是早年参加革命的,革命胜利之后,他生活比较富裕了,空闲没事了,他怀念以前的革命岁月,把它写下来。他拼命想传达革命理想,在里面经常喊革命口号。一个地主出场了,一个鬼子出场了,他就写这人怎么怎么坏,这样写恰恰没有趣味了。很多革命作家的故事很好、题材很好,就是写不好,稿子到了出版社之后,幸亏新中国那时候是很扶植工农作家的,出版社派了大量的编辑帮他们改,派很多成熟的作家帮他们把故事改得更好,改得更引人入胜。很多著名的作品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像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原来没有写得这么好,就在于曲波选择了跟古龙一样的路子。像古龙这样的作家其实他在生活中是很有感悟的,用一个词叫苦大仇深,社会让他受了这么多的伤,他应该写出精彩的、伟大的作品来。但是精彩的作品写出来了,还没有达到伟大的程度,但是这样反而更好,不然成为另一个梁羽生也没什么意思。古龙恰好留下了另一种拙异的、怪诞的,跟金庸、梁羽生小说完全不同的一种武侠小说。

《金庸者谁:北大金庸研究课堂实录》 作者:孔庆东 著
来源:北大出版社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