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
这次路过合肥时见了作家苏北,承蒙他招待并赠送一套他的作品集,十分快慰。归来翻阅他的著作,那一篇篇深情回忆他与汪曾祺交往、受汪先生亲炙的文字,温婉迷人,十分令人钦慕。
众所周知,苏北是汪曾祺晚年的入室弟子,与“老头子”和汪家人都“混得厮熟”,受到汪老的指点后在创作上有明显的精进,乃至在行文中有时也能看到汪氏风格。可以说,没有汪曾祺就没有后来的苏北。苏北很早就认识到汪曾祺在文学上的创造性价值和之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在结识汪老之前,他就将汪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晚饭花集》一字一句地抄录在笔记本上,结识以后更是一直追随和学习汪老。汪老仙逝后,苏北还常常“忆·读汪曾祺”,真可谓“一‘汪’情深”,令人感佩。
我也是很早就读汪曾祺的。大约是1981年,我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一册1980年第十期《北京文艺》,上面刊载了汪曾祺复出文坛的第一篇作品《受戒》。我当时虽然只是一名乡下的初中学生,读完之后也有一种“惊艳”之感。我甚至觉得那整本杂志只有这一篇文章活生生地立了起来,在我眼前上演了一出活剧,从此再也不会把它忘记——这就是一篇好文章的魅力吧。我还记得小说中小和尚唱的那首带一点“荤味”的歌谣“姐儿生得漂漂的”,写出这样一个小和尚的爱情故事,在当时可谓相当大胆,有些“惊世骇俗”。现在想来,汪老对突破旧套、解放思想是作出了贡献的。后来,我还读到了他另一篇名作《大淖记事》,也觉得十分隽永有味,从此汪曾祺这个名字便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我读书的人民大学我还见过他一面,准确地说,只是比较远地望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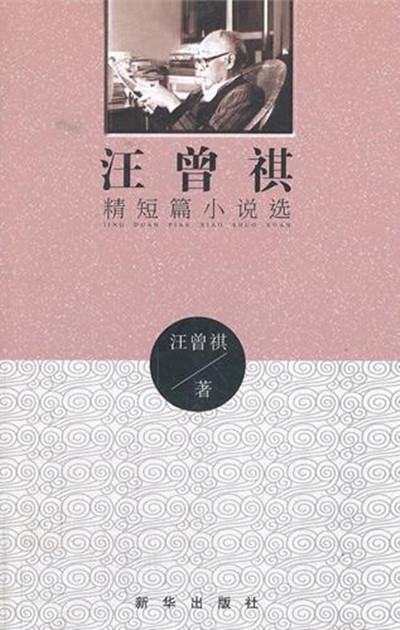
那应该是1993年冬或1994年春天的事,确切的日子记不清了。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来钟,我上完自习回宿舍路过一幢教学楼,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外,看到里面灯火明亮且坐满了人,连过道、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而讲台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矮小的老人。我心知这是在搞讲座,但不知是谁在讲、讲什么,于是向门口一位听讲的同学打听,他告诉我是汪曾祺在讲新时期中国文学和自己的创作。哦,是汪曾祺!我费力挤进了教室,定睛一看,一个黑瘦的老头儿坐在讲台上,半蜷缩着身子,脸上几无表情,似乎在听底下某个同学提问;而他的面前还放着一只拳头大的陶壶,不知那里面是装着茶水还是装着酒,我猜想很可能是酒——我似乎读过有关他爱酒的文字。因为来得迟,我赶上的只是讲座尾声的交流互动阶段,又因为离得远声音小,听不清楚,所以我便失了兴致,转身退出。但因为有这么个讲座,见到了我闻名已久的名人,我感觉这个夜晚有了微微的暖意,连空气也格外清新。
我后来一直搜罗汪老的作品来阅读,而且越来越喜欢。2008年前后,我购买了收录他作品最多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这样,手头总算有一套比较齐全的汪老的著作了。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想编几本汪老的著作出版。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被我等到了,我与汪老的女儿汪朝老师取得了联系,随后编辑了一本《汪曾祺游记选集》。我写了编后记也写了书评,表达了我对汪老的敬仰和对他文字的迷恋。接着我又编了一本他的《小说自选集》,后来又编了《汪曾祺精短篇小说》。其间承蒙汪朝老师补充了她新发现的汪老的旧作,使这些书不仅仅限于“炒冷饭”而有了新内容,这是我要衷心感谢的!
每次去汪朝老师所住的高知楼,坐在她收拾得干净雅洁的客厅,我都百感交集,后悔过去没有能够多亲近汪老先生,哪怕跟先生多说几句话也好啊!幸好还有他的书在,他那独具风采的魅力也将永存世间。
作者:李成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