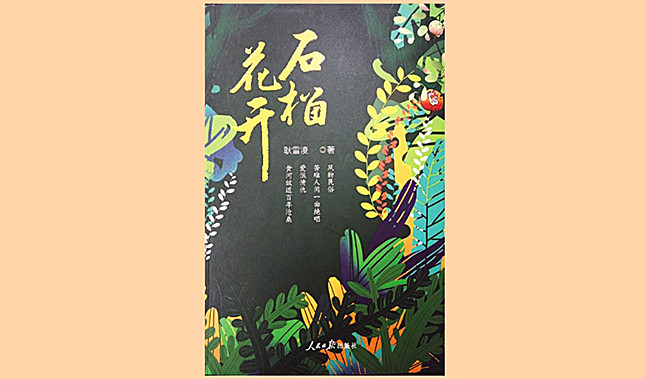
▲《石榴花开》 耿雪凌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耿雪凌的《石榴花开》是一部以黄河故道地域文化为背景的乡土长篇小说——所谓黄河故道,就是黄河的旧河道。黄河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历史上的黄河曾经多次改道,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2600年间,因河床的不断增高,或者各种人为因素,黄河曾经决口1500多次,经历了26次改道,可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而黄河接近半数的改道,鲁西南总是首当其冲,其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生活在这片苦难土地上的鲁西南人,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灭顶之灾,一次又一次地绝地重生。黄河改道既为鲁西南人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同时也让这片土地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地貌,从而孕育出独特的故道文化。耿雪凌即以这种独特的文化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家族苦难的生存,讲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不甘与抗争,并将他们人性的本能赤裸裸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小说起始于1938年6月,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堤的前一夜,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石榴,她是灾难的幸存者,也是一个一生生育了19个孩子的女人。对于生活在鲁西南,具体说生活在单县的黄河故道人而言,1938年6月并不仅仅意味着黄河荡决与洪水滔天,同时也是日寇进逼,土匪割据,各种势力相互拉锯,以及蝗灾、旱灾、饥荒等一系列天灾人祸的开始。然而,在那个人命贱如草芥的年代,活着尚且不易,石榴却以自己矮小的身躯顽强地孕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尽管命运总是与她作对——家乡被淹,母亲和哥哥生死不明,新婚之夜遭遇抢劫,公公婆婆双双死去,接踵而至的还有灾荒饥馑,流离失所……但石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坚强,活得明白。石榴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也是同样。比如用鼠药毒死自己男人的小麦,跳湖自杀的大麦,她们陷入了与同一个男人的畸形之恋中不能自拔,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她们总是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即便生活困苦难行,她们依然显示出一种无畏的执著与力量,命运压不垮,苦难打不倒,随时可以走出低迷,焕发生机。她们的生命如同黄河故道边生长的野花,盛开,凋谢;时而温暖,时而冷酷;既有精彩,也有悲哀,这其实正是黄河故道人的生存状态。
是的,黄河故道人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爱和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跌打,挣扎,摔倒了,爬起来,擦干血泪,继续前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每个人的命运都很曲折。在耿雪凌笔下,黄河故道自是莽莽苍苍,一望无际,两岸各种各样的树木茂密繁盛,河底生长着芦苇和蒲草,呈现出一种神秘的样貌,氤氲着人们带有神异色彩的浪漫想象。虽然肆虐的洪水时时威胁着黄河故道人的生存,但这片土地待他们毕竟不薄,丰年不必多说,单是细腻的沙土窝,既可以当床,又是孩子们天然的尿布。在耿雪凌笔下,黄河故道人的结局往往是悲惨的,但他们的生活本身却充满了喜剧氛围——她写蝗灾,本来有着悲壮的色彩,却因了两个孩子的玩笑嬉闹,变成了一个充满喜感的场景;她写生育了19个孩子的石榴,说“石榴那块田地,有种就生根发芽”,像极了孕育一切的大地母亲。这或许就是黄河故道人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泼辣,狡黠,具有双重性格,不如此则不足以讨生活;他们拿得起,放得下,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于他们也不过尔尔,一切都是活着的需要……这些复杂而多面的人格,造就了他们大悲大喜的人生。
乡土文学的要义,首先是深深地根植于乡土,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有深情,有认识。耿雪凌是土生土长的黄河故道人,她的小说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是语言。耿雪凌熟稔这片土地,她不仅对乡土语言有着娴熟的把握能力,对方言俚语的运用也得心应手、恰到好处。读耿雪凌的小说,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扑面而来,透过这些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字,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黄河故道人真实的日常生活,听到他们的言谈话语,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既生于斯,长于斯,也歌于斯,哭于斯,他们的所思所想与这片土地密切相关,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尽管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面前渺小如尘埃,卑微如草芥,但在他们的生命中,却从不缺乏源自人性本能的大欢喜与大快乐。
黄河故道原本是一个有灵性的世界,天地有灵,草木有灵,万物有灵;黄河故道同时又是一个灾难频仍的世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苦难其实更像是一种磨砺,让他们坚韧、隐忍,让他们冷酷、决绝,这一切都是为了活着——只要活着,他们的生活就算成功,他们的人生就是喜剧。而石榴则更像是一个象征,黄河故道人的屈辱与伤痛,不甘与抗争,坚忍不拔,生生不息,都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耿雪凌以泼辣、粗粝的文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黄河故道人野性而剽悍的人格魅力。
作者:王淼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蒋楚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