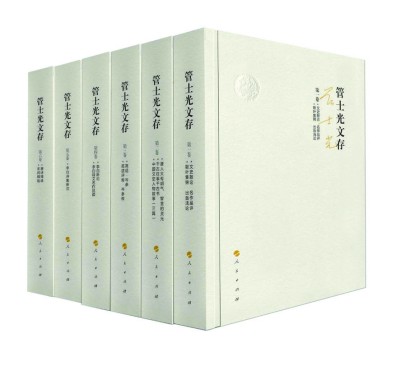
《管士光文存》(六卷本)
管士光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向晨
前日到房山琉璃河访友,春日迟迟,梨花刚刚谢幕,海棠风华正茂,有国产的,也有外来的,白色如鹅绒,红色如绣球,好不养眼。走到近前,树下土垄密密匝匝花瓣尽覆,白的像厚厚的落雪,红的像美艳的锦毯。友人们不禁感叹,不早不晚,真是好时候,树上花有形,树下花有色,相得益彰,手机拍照电都不够了。
看花的心得,竟然在读书中得到另一种呼应。
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这是唐人张渭写的《早梅》,描写了早春的小桥流水边突然看到一树寒梅上满是“白玉条”,怀疑是残雪冰花,近看原来是梅花已经开了。
另一首非常熟悉的《梅花》是王安石写的: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是梅花与雪本身难分难舍,还是文人与梅花同气相求?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这是宋代诗人卢梅坡的《雪梅》,一段雪VS梅的比拼中,看得出诗人两厢爱惜,生怕判失公允,但爱梅之心,未得掩饰。
诗歌史上,花是一大主题,梅花不是海棠,但心得相仿。古人赏花不仅仅为了悦目,更重要是赏心。“咏梅诗,同其他咏物诗一样,都不仅要求形似,而且更要求神似,即所谓‘以貌取神’。清人田同之《西圃诗说》云‘咏物贵似,然不可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
不禁想到,与今人相比,赏花这件事是不是有点过于严重了?
此言差矣。其实中国古典诗词非常迷人之处就是古人超凡脱俗的“多媒体”表现能力。比如画面感,比如抽象化,比如夸张,比如联想,多么像形、色、音、味、质感同在的5D影院?
以上这些感想,来自一篇长文《古诗与名花》。梅花之外,该文还写到了月季、牡丹、荷花、菊花。这五种花可能是唐宋诗词里的“名花TOP5”吧。文章非常细致地梳理了唐宋时代的咏花主题诗,不仅精选有代表性的篇什,评述中还捎带出大量有特色的诗句,不仅详解了背景、内涵,又剖解了艺术性,对于有赏花经验的读者,不啻于一次专享服务了。
文字的作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先生。他年轻时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刘忆萱教授,又深得冯其庸先生教诲,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获得了深厚造诣。2017年1月,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六卷文存,出乎意料的是,厚重的作品并未打上明显的出版人标签,除了名社经验版的“出版浅论”,三百五十万字的百分之九十展示的是其耕耘古典文学田园的功力与情怀,有边塞诗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的简传、评传,又有《李白新论》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传记性研究,也包括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历史学的系统框架性的爬梳,而选诗、注诗、解诗更像一种绵长的兴趣,贯穿着他的写作生涯。
花与古诗,体现了温柔浪漫的审美,而在另一面,管士光对反抗性的文学力量,似乎更加敏感。对高适、岑参的书写当属于此,而某些闺怨诗经他释义后则显得不同凡响。比如解读李贺的《宫娃歌》,他特别强调“大不一样”,不仅仅有怨旷之情。诗中的宫娃似乎已经对君主绝望了,在“怨”之外甚至有恨——“不仅仅是等待君主的眷恋,而是要求冲出深宫,获得人身和精神的自由。”在品评花蕊夫人徐氏的《述国亡诗》时,他甚至这样写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除了表达诗人亡国的沉痛心情,徐氏用‘更无一人’与‘十四万人’对比,来夸张后蜀将士的无能和误国,首当其冲者,自然是孟蜀的君主!”经典文本中批判性的基因更容易跃入他的眼帘,从艺术表现而言,力与美的结合总是更能震撼人心,而浪漫主义正是两者的黏合剂。
这一点还体现在管士光六卷文存的第四和第五卷——《李白新论》《李白诗文名作品读》《李白诗集新注》几乎涵盖了从诗人到作品注释、解读、研究的全部领域,足见其对李白用力至深。这里的起因固然是管士光读研时选择的研究方向,更重要的还是李白诗对他具有的无穷吸引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左”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文学研究,管士光在对李白的政治思想刨根问底时有所突破——一些研究者总是强调李白的反抗性和作品的思想性,他却下了“李白的立场仍在李唐统治集团那一边,但他的诗文‘灌输了对于现存秩序永恒性的怀疑’(恩格斯语)”的结论。在对《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本溯源》一文中,他从“风格即人”理论出发,分四个维度分析李白创作风格的形成:流徙色彩浓厚的家庭给诗人成长经历中注入了游侠般的急公好义、豪放无畏的性格;一生游遍山水自然的经历陶冶了诗人的自由灵性和想象力;交友甚广、愤世嫉俗的道家思想培育了他“不屈己、不干人”的作风原则;宏大的政治理想遭遇黑暗现实时,不仅没有颓废、怨叹,反而使他对仙境的幻想越丰富、越浪漫,这种向往和描绘植根现实生活,拉伸反转出夸张的表现力。
李白布衣仗剑壮游,一生无数次踏上说走就走的旅程。他的生活方式或许正是盛唐之风方能给予的。谈起李白不能不说唐人,谈起唐人又不能不说“胡化”,《唐人大有胡气》这篇文字便是管士光潜心研究李白的必然延伸。
“胡气”是指来自异域的文化和风习。《唐人大有胡气》研究了唐代这个“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的时代”的对外开放问题。管士光从政治、经济、人口、国际关系,社会、文艺、宗教两大层面七个方向入手分析,“中国既安,四夷自服”(魏征语),唐朝君主通过 “天可汗”之名,向中亚和西方的民族和王国传达了令他们信服的价值观,对胡人采取具有吸引力的开放政策,鼓励他们前来中国经商和传播文化。在《“胡气”——一种社会风尚》一节里,作者以李白诗“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留别广陵诸公》)以及高适诗“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走马”、岑参诗“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等揭示当时的诗人、武将和高官的尚武之风,唐人的生活喜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气”的引领。管士光挖掘史料,指出大量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将舞蹈之风传入长安的宫廷显贵中。据《旧唐书》和《唐内史》记载,中宗宴请大臣,每人均须出节目尽兴,宰相杨再思跳“高丽舞”,国子祭酒祝钦明跳了“八风舞”,工部尚书张锡跳“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跳“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跳“黄麞舞”。文武官员舞技娴熟说明长期练习,舞名大多为舶来品,确凿地证明“胡气”在当时不仅时尚,而且因为皇帝的偏好,造成一定的主流化倾向。
管士光的学问打上了唐代文明深深的烙印。他盛赞道: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蓬勃向上,人们从上向下充满了骄傲感和自信心,对于异域异族不仅不惧怕和排斥,更多的是好奇。书中引用鲁迅的话:“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进而推出“唐人大有胡气”的原因和意义。
作为一位做书人,管士光先生主持和参与过许许多多的出版工程,可谓予人好书,手有余香。《管士光文存》彰显的却是一位学者和读书人的拳拳之心、首丘之情。可以想见,在古典文学的花海中率性徜徉,或许是一个令人不舍得觉醒的梦境,尤其是在花开花落最美时,缤纷浪漫怎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