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之际,"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的社会风气弥漫江南。江南八府一州中,除中心城市苏、杭而外,像松江府、县城这样的二、三等城市,也见"俗好侈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宴会,竭力以饰观美"的奢靡之风盛行。华亭人范濂在《云间据目抄·风俗》中慨叹:"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岁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虽说傲视当世,时常讥讽时世的范濂,言论相对偏激,就连同郡乡绅陆树声,在其关押释放后也好心告诫说:"别再写了,否则要遭杀身之祸。"但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府城奢靡之风,已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松江社会生活,并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差异和言行方式等精神思想差异上真实反映出来。这些差异在范濂的《云间据目抄》、陈继儒纂的崇祯《松江府志》、叶梦珠的《阅世编》记风俗中均有详实记载。值得一说的是,晚明著名文人、隐于松江东佘山的陈继儒,不仅针对"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的浑浊世象,辑录编撰了人人读后皆有助于"解醒"的《小窗幽记》,而且慨然答应出山纂修崇祯《松江府志》。在这部府志所载的风俗卷中,史料详实地记录了松江"俗变"情形,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俗变"开门见山,在第一段中便发出崇尚节俭,要从士大夫带头做起,以影响社会风气好转的时代呼声。这一点,意义相当深远。

崇祯《松江府志·俗变》,釆用前后对比表述方式,从二十四个方面系统陈述明代中后期风俗流变详情,大抵内容如下:
顾文僖公(顾清)曾叙述风俗说:松江之风俗,见于史志者,有几次变化。观察这种变化,可以知晓世风民情。现在我姑且记录这种变化。变化大概都是从有势力有声望的大家族开始的,上自婚丧宾祭冠履服饰,下到细枝末节等风俗都有变化。感慨世风日下者,想办法要移风易俗,难道是无意义的吗?躬行节俭,请从士大夫始!

乡饮之变。按照礼制规定,致仕还乡的官员及民众中年高德劭或者有品行的儒生,行饮酒礼,因此由有爵位或者年长有德者主持。年轻或者德望不够的人为宾,比宾再次一等为介。通常来说,府官为主,官佐僚属按照官阶高低坐于西,耆老儒士按照年龄大小坐于东。教官端起酒杯,生员读《大诰》及《大明律》,听完开始行酒,五行、七行或十行,然后作揖拜过之后离开。现在乡饮不一定非得有大官或耆宿,有官方来主持安排。按照传统的做法,有未参加乡饮者,可以把整桌的酒菜送过去。

婚娶之变。婚礼的前一天,将嫁妆送到男方家里去。现在改为男方迎接嫁妆,在大路或十字路口迎接脂粉、帷帐、被褥、枕席等,吹打鼓乐在前面引路。妇女乘坐轿子与亲人回家,名曰送嫁妆。金珠璀璨,士大夫家往往如此,以夸耀嫁妆的丰盛。又有新娘子喝交杯酒时,头上带着用彩纸剪成的花髻。男家所准备的礼物,用亲人挑着竹筐盖好送过去,名为挑方巾。开始饮酒三行,此为俗礼,不知始于何日,一直沿袭至今不可废,知礼者应当商量一下革除它。

丧祭之变。吊唁者都用降真香祭拜,丧家都设木架,香就放上面。一天中来烧香的人不断,妇女聚在一起号哭,但并不一定是全因悲痛。人死后,按照死者生前等级身份,要用绛色帛制作一面旗幡,上面以白色书写死者官阶、称呼,用与帛同样长短的竹竿挑起,竖在灵前右方,称之为铭旌,也有用银箔装饰的。入殓后,以竹杠悬之放在灵位右侧,下葬时取下放在灵柩上。香和祭品少了,便被认为是简陋。将殡葬时,则要准备迎祭,罗列陈设贡品百案,名曰九煎,剪彩纸为人物、花果、纸佣与从,亦为百数。也有优伶装演故事,鼓乐喧闹,都在丧所迎候,容易冲淡哀伤的氛围。因此,君子都讥讽这种俗礼。

赠賻之变。古时丧礼有赠賻之仪,谓助以货财。如凡民有丧,亲朋一起救助。一般情况下,贫家尚未遭丧事时,都被医药等费用所窘迫,亲朋根据自己的情况为之扶助,以资缓急,使他们能够拿出粥饭待客,棺椁葬亲。今士大夫既不受赠,而贫家亦不复致賻。今准备一些纸钱、贡品,写上自己的名字,一拜之后随即离开,古意荡然无存。

宾宴之变。酒席大多丰盛,蔬果之外,杯盘碟碗,还有各种菜肴。遇到长官、上司等,乡绅也要作陪,更加器用精美,菜肴百种,遍陈水陆,还要选优伶演举重,金玉犀角,递相行觞,或重设酒席到别院。张华灯,结火树,热闹到天明,风俗如此,贫家也示人以奢侈,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

冠髻之变。明朝初年所用巾帽,帽以六瓣合缝,下缀有檐,此种形制应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制,有人说这寓意着六合一统的意思。杨维桢朝见朱元璋时,曾头戴方巾,称为四方平定巾。商文毅公被召用时,也是以此巾觐见。今士人已不大看中唐晋时的形制,少年都戴纯阳巾,为横折,两幅,前后覆盖为披巾,披巾后一幅又如将巾,以蓝线作小云朵,缀在旁边,再将披着的那一部分缘起来。以蓝为云巾,前系玉器,作小如意,为玉结,形制各不相同。女子髻也有时变,近来越来越小且低,如发尾有云儿覆盖后颈者称为纯阳髻。有梁者,为官髻,有的缀了珍珠,有的在后面垂了丝带,也有的佩戴龙凤翡翠饰件。古人虽卿相致仕者,入乡里的大门,则用肩舆、方巾。贤妇人椎髻,力作有不弃蓍簪者,这已经不多见了。

服饰之变。男子广袖垂大带与身等。组织花纹,新异如雪梅、水田,凡数十种。女子衫袖如男子,衣领边缘用绣帊,如莲叶之半,覆盖住肩膀,曰围肩,间缀以金珠。裙用彩绣,有史志记载挑线织金,大家都认为很丑,工艺也很拙陋。然而贫家男女,形鹄衣鹑,田巷相望,得求败絮,也当做取暖的东西,令人怜悯。

履袜之变。旧制,民间多用布履,有镶履为二镶三镶之制。色用青蓝,或红绿,为朝鞋。今履用纯红,及各色,镶者少用。又有道鞋、毬鞋、靴头鞋,其面浅而稍阔者,曰童鞋。有彩线组为花者,为网绣鞋。也有纱制的鞋,用皮金装饰的。有裂布而制成布条鞋。袜的形制,一开始比较窄,后来越来越宽大。短面,让穿鞋子更舒服,多有绫罗绸缎纱为材料。市中有造袜客,做买卖生意,称为尤墩布袜。

组绣之变。旧有绒线,有刻丝,今用劈线为之。写生如画,也有用孔雀毛做成草虫的。近绣素绫装饰为屏风,其价值不菲。也有堆纱作折枝,极生动,也很珍贵。顾绣在斗方之间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是其他郡所没有的。

布缕之变。史志上记载为三梭布,后用云布。今有七寸、九寸标准的布。官布又有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为非常绚丽的织法。今京城染青的标准,皆新改放长名色。旧贵尤墩布,以其厚且重,不便穿制。这种织法的人也少了,只有真紫花布,大家都喜欢用。

染色之变。起初有大红、桃红、出炉银红、藕色红,现在为水红、金红、荔枝红、橘皮红、东方色红。起初有沉绿、柏绿、油绿,现在改为水绿、豆绿、兰色绿。起初有竹根青、翠蓝,现在改为天蓝、玉色、月色浅蓝。起初有丁香、茶褐色、酱色,现在改为墨色、米色、鹰色、沉香色、莲子色。起初有缁皂色,现在为囗色玄色。起初有姜黄,现在改为路子黄、松花黄。起初有大紫,现在改为葡萄紫。

几案之变。起初只用官桌,有并春即是小副桌也,规格高的演戏则添加上去。今家有宴几,有天然几。书桌以花梨、瘿柏、铁力、榆木为之。椅起初有太师及栲栳圈、折叠之样式。现在木头也都不养,甚至有用离奇蟠根为座及榻的人。

舆盖之变。士夫舆都用福建的做法,此宋航海时所遗留下来的样式。初青绢伞,今俱用蓝色;黄伞则用金红黄色。其檐加倍的深了,向来为乡绅出入所未曾用过的。至嫁娶,初时,必先世仕族,在中间用一盖前导,或青或黄,要根据官阶大小准备。现在一般的老百姓和小官吏,都用黄盖,觉得很美观。

舟楫之变。起初有航船、游山船、座船、长路船,现在改为浪船、楼船,朱栏翠幕,干净得像精美的房屋一样,游人往往在里面设酒席招待亲朋,远近都可通行。小舟称航船跟以前一样。其泖西舟人所驾的小船成为水荒船,言低乡无田可种,以驶船为生,因此命名。

室庐之变。起初只有庭室堂楼。乡绅大夫有不少居住在城外,如南郊两张尚书,东郊孙尚书,西郊顾尚书,相关的衙门也在所居住的地方建设牌坊。现在缙绅大夫都喜欢居住在城内,旧的官员宅第转展相售,居必巧营曲房,栏楯台砌,点缀花石,几榻书画,都比着华贵奢侈。旧志记载风俗尚清雅,饰玩好,犹仍至今。开国初时的旧房子,基本上都差不多没有了。

园林之变。起初以前的名流富人居住的地方,一般粗有园亭,与贫交故旧,往来盘薄,或读书赋诗,如顾文僖傍秋亭、近陆文定适园,并没有高台名楼。后来,才有运石开溪,大兴土木,花费多达千万,仅供人游览。后来又用黄石叠山,向横云半为石工所凿,今山神更加痛苦了。

迎送之变。起初子弟入学及参加科举考试者,相关衙门按通常的做法,用彩绒花,披红药绢,及红旗一对,有乘肩舆,也有步行的人。今新进送学,大家族或者官宦人家,多乘马,张盖,罗绮绸苎,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龙以炫耀。亲戚们也争着用酒礼花币欢迎,交错于途。自府学校到文庙,谒拜。再各回家设宴以待应试归来的进士。南归,舟至西墅,迎接也如是。读书人刚刚正要进步,应当教给他们俭约。士大夫不应当用这样奢侈的方法训导子弟也。

缇帙之变。起初乡大夫诸生与郡县官员交往的人不多,近来动辄用册叶锦屏。册诗则请代作,以士夫署名。也有人摹石刻棘,装为墨帖者,花费了不少钱。每人收一个锦屏,如果有一百人的话,光装潢之费,就要花数十金。主者偏索授纪网,纪网因而为利,且藉此阿谀奉承上面的官员。于是有缺少德行的人,身犯大罪,甘心锒铛入狱甚至为此丧命,也一直不后悔。以前松江知府许维新刚到任上时,府里的士子也有送锦屏者。知府收录了他们的文章,退却了他们的锦屏。士子们坚持恳请他留下,许维新让他们交到府学校暂收公用。后来不得已,士子们惭惭地退下了,终许维新任上,再没有胆敢以私事结交他。

楮素之变。之前见古名家书翰,都用素纸,间杂地也用宋笺、谭笺、粉笺、罗纹笺,写大字则用疋纸而已。近来渐渐有人用金笺、砑光绫、素绢,诸帧轴。而交际多用全柬。婚用销金。余短笺单幅,绘花绝巧,日异日新,殊非大雅。

巫医之变。旧志记载高启《里巫行》云:“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现在巫祷都以宰杀牲畜为祭品,陈列凡十数,桌为叠台,遍请诸神,歌唱到天明。又用歌童,时助以曲鼓乐,中间还有献花献币,病者小差,则以占卜之验、祷赛之灵。转相愚感,即使贫困的家庭也勉强跟着这样做。医生起初都是顶帽步行,儒家有的也曾当过官,见到有司官员才戴巾。现在都乘车或轿子,络绎往来,其中以医术成名者也不少。

方外之变。僧有禅,有教,念珠衣服都不一样,出则穿之曰偏衫,顶高帽。今方外皆铁色便衣搭帽,冬用幅巾,或观音兜而已。初应教茹荤,间有斋者。近初染剃,有志少年,皆习禅行,也都持斋,写字学画,为清课,这又是经常变化的。

优剧之变。起初大宴会,才开始演戏,名曰步戏,都用旧的戏本。宴女客尊亲,则用傀儡戏。今翻为新剧,且必妓女,应接不暇。旧志载孙华孙竹厅《山歌》云:"城里歌姫日赴筵,上厅角妓似神仙。吾家每欲延佳客,十日前头与定钱。”则歌姬就开始有了。现在更加华绮,只有官府宴席不用。

声妓之变。起初有粗乐、细乐,后来又引进了胡拍、提琴等乐器,将小乐器互相配合成“十锦”音乐。规矩也稍微有些变化,如有的宴会邀了妓女,与宾朋坐在一起,当作雅客对待,好像不是勾栏中人了。

僮竖之变。初士夫随从,皆青布衣,夏用青苎,冬有衣铁色粗褐者,便作盛服,但是不经常用。近僮竖皆穿黑色罗绮,至有天青、暗绿等色。中裙里衣,或用红紫,见宾客侍左右,都不觉得奇怪。虽三公八座,间亦有之。凡一命之家,与豪侈少年,都比着豪华奢侈,也没有等级规矩,他们的家法门规也就可以知晓了。

上述可见,由官府邀请陈继儒等出面纂修的崇祯《松江府志》记俗变,与范濂《云间据目抄》、叶梦珠《阅世编》记松江风俗之变,内容近似,但说法上相对平和。例如范濂说他生活的时代,松江城里有不少来自安徽的小木匠,忙得不亦乐乎。当地"纨绔豪奢",以为椐木不华贵,"凡床厨几桌,必用花梨木、瘿木、相思木,及黄杨、紫檀,极其贵重,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范濂痛恨奢靡风,习以讥讽笔调斥之,其《云间据目抄》载:"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皆鄙为寒酸,即家无担石者,亦必用䌷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帮闲恶少尤甚,日从典肆中觅旧绒旧缎,翻改新制,思与豪华公子列坐,亦可嗤也。"细品这段文字,极具讽刺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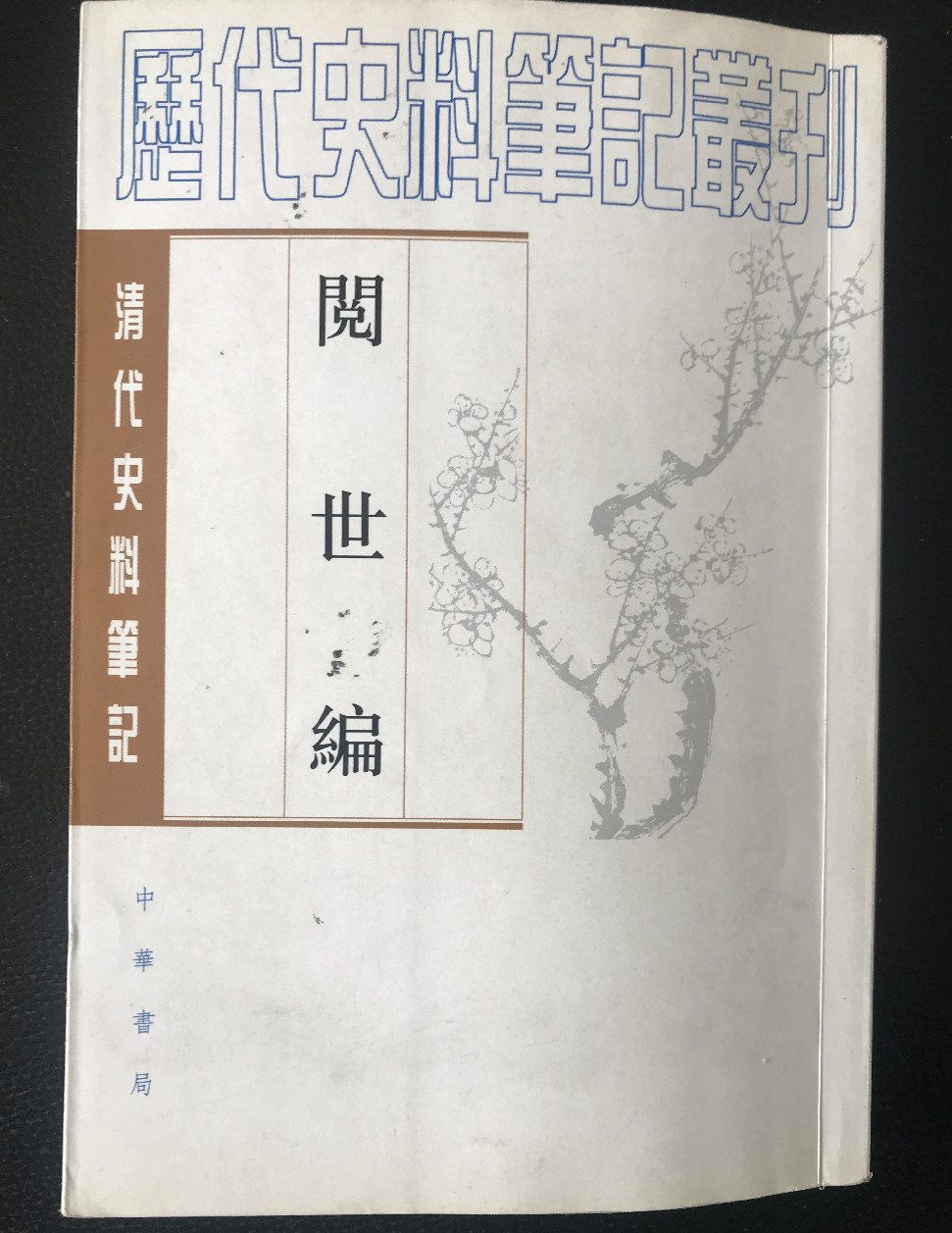
生于明末的叶梦珠,明亡时21岁,主要生活经历在清代初期。他在《阅世编》中回忆说:"冠礼,古人最重。予幼闻父执行冠时,尚邀冠宾,三加元服,一如古礼。及予所见,初冠者出见亲长必拜揖,亲友见之亦必揖而称喜。余冠于顺治之初,犹习旧文也。近来三岁童子即加元服,与成人无异,不择吉日,不谒家祠,其设香案,参天地,拜父母,盛服筵宾诸礼俱废,古制荡然矣。"如果说范濂对松江世风日下,表露出的是一种直言不讳的痛恨情绪,那么,叶梦珠对地方古礼崩坏,则更多流露出了痛惜情怀。此外,叶梦珠还具体记录了当时"宴会"菜品情形,云:"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

风俗是一地百姓相沿积久成习的文化现象,一旦落地生根便具有相对稳定性,然而,晚明包括松江在内的江南诸府,时风嬗变,尤其是奢侈风习气势如火如荼,委实令人在刮目相看的同时有些看不清、看不懂了。话说回来,一种能够从城市刮到乡村,令人感到无法抗拒的俗风流变,背后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只是言长纸短,就不细加赘述了。在此,我想说的是,回首晚明之际,恐怕是"崇俭"与"崇奢"两种对立观点斗争得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其中又以明代大儒上海陆深之子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一书中提出的"奢能致富"的论点最具代表性。

▲ 陆深画像
在对待世风日奢这个问题上,如果用有其父必有其子来评说陆深、陆楫父子,则不然也。俭朴持家、洁身自好的陆深,看到"风俗日坏,海滨尤甚",教导约束其子"吾儿宜力行古道可也",并要求陆楫做俭朴的榜样,以影响世风。他对儿子说:"世道如此,正要吾人力挽回之。"这与范濂哀叹奢靡之风"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已无还淳挽朴之机",似乎更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历史有时候会出现造化弄人的一幕,陆楫非但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行事,还背道而驰地在其《论崇奢黜俭》文中表明"奢能致富"的鲜明主张,认为"节用"不利于生产发展,节财并不能使民致富。不可否认,江南奢侈之风,对于冲击封建伦理道德,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城市人口就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过往的史实证明,奢靡风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构不成因果关系,其助推经济发展只是暂时的、表面的,一旦过度泛滥开去,攀比、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终将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毒瘤。

正因奢靡导致社会风气发生种种变异,使得松郡诸多有识之士忧心不已。华亭人何良俊,在其《侈汰》中认为,孔子对于攒越传统的行为都表示否定,日下奢靡习俗必遭惩罚;甚至预言那些"侈汰之徒",如果不加收敛,灾难将会接踵而至。曾在京师任内阁首辅多年的徐阶留下了《世经堂集》,其中就有"请禁奢侈"的奏疏。这份奏疏将奢靡的源头指向朝廷和各部大臣,谏言管束朝廷大臣,如有违者,绳之以法。徐阶的奏疏,谋略周全,其中有周密计划和具体步骤。但令徐阶始料未及的是,他的上奏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此外,云间名士李雯等分析国势,上疏论救国之策,认为禁奢已为头等大事。他满怀信心期待朝廷纳谏昭告天下,结果也是如风不知归期,不了了之。所以,在晚明的世象里,既看到了一种所谓的繁华,同时也听到了一种禁奢的呼声,但走向没落的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因此,世人最终看到的是,前后延续276年、历16帝的大明最后一任崇祯皇帝,自缢于紫禁城北面煤山(景山)的历史一幕。综上所述,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它不仅是最好的教课书,而且是最好的清醒剂。
作者:尹军
编辑:邵大卫
来源:人文松江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