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洪文达(1923.8.2—2014.2.5),经济学家。安徽泾县人。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系,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班。1950年—1953年在华东财经委员会工作。1954年调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1956年调复旦大学,任经济学系副教授。1979年,参与创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曾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等职,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等。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与世界经济的教学研究,联合主编《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等。
让每一位认识洪文达先生的人给他画张像,共同点便是“那位满面红光,讲话中气十足,关爱学生的经济学人”。即便在病榻之上,即便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依旧是那位声如洪钟、乐观豁达、豪爽健谈的洪先生。2014年3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诸位经济学者和洪先生的学生们坐在一起,缅怀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追思会的名字贴切极了,“人文载道,通达一生”。
1923年8月2日,洪文达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学时代曾入读著名的苏州中学。1938年,教育部在重庆江津德感坝设立了以安徽籍流亡师生为主体的“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后改名“国立第九中学”。少年洪文达便也辗转到了重庆,成了“国立九中”的学生。此时的洪文达便有机会接触“青年自学丛书”(生活书店出版)等通俗的社会科学启蒙著作。在“国立九中”,洪文达有一位同桌,他的名字叫做邓稼先。
会考时,洪文达成绩很棒,排在理科前十。大概是心情大好,便约上同学一同出游了,以至于填报志愿时,人并不在校,只好委托老师代填。或许是老师觉得他的化学读得不错,便替他填报了“中央大学”的化工系。用洪文达之子洪新先生的话来说,“彼时的化工学科,其热度大概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系”。而在那个年代,“中央大学”的化工学科无疑是国内最好的。手握试管、烧瓶,洪文达却越发信仰“经济救国”的理念。于是,他毅然弃理从文,远赴汉中,入读西北大学经济系。
洪文达一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接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却是从读文艺书籍开始的。他喜欢旧俄现实主义小说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最“走心”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些著作激发起一个青年人改造社会的热情,也就自然地推动他去接近马克思主义。在西北大学求学时,课堂上老师讲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课程,业余时间他却捧着《反杜林论》《资本论》不放,一心钻研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他有观点,更重要的是观点后面跟着逻辑、跟着文献”
1950年,洪文达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教师中的一员。同年,他去教职,入华东财经委员会,先后任办公厅秘书和第二办公室私营企业组负责人,同时在沪江大学和上海财院兼授经济学。其间,与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有了诸多往还的机会。
1954年,洪文达调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一年后,任该校副教授兼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洪先生重新登上复旦大学的讲台,执教经济学系,任副教授,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洪文达的教学和科研重心开始逐渐向世界经济学转移。从此,开始了其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耕耘。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群心中有梦、脚下有路的年轻人,带着憧憬走进了大学校园。对于洪文达而言,无疑也是一个的新的开始。
“洪先生健谈,上课很吸引人。”忆恩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说,“他有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观点后面跟着逻辑、跟着文献”。
77级大学生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同寻常的一群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纪、经历都不尽相同。“77级上课常常是没有讲义的,大家都是成年人,课堂上更多是思想的交流。对于老师而言,恐怕只有这样才能‘镇得住’那些‘大龄学生’。当然,那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施展才能的机会,所谓‘教学相长’嘛。”在华民的记忆中,洪先生的观点很新、很鲜活,“往往是他昨天晚上思考的问题,第二天早上就拿到课堂上分享了。”
“越是理性的人,越是懂一点东西的人,越是开放”,这是当年洪文达对汪道涵先生的评价。事实上,他大概也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身后才会不乏“当时经济系,思想最解放的是洪老师”“洪先生对待学术严谨认真,思想开放,与时俱进,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眼光”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末,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郑励志和洪先生一起去日本参加研讨会。“洪先生每到一所大学都积极热情地与学者交流,关心新鲜事物,关注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希望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向日本学习。”三十几年过去了,郑励志依旧记得分明。
洪文达主张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西方经济。他的思想萌芽、形成在中美建交以前,这在学术界、在理论界都是比较早的。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之中,他始终要求学生睁大眼睛去看世界,“不看世界,怎么看得懂中国”。“研究经济就要有全球眼光,有世界眼光,然后要有自己想法,这便是洪老师留给复旦世界经济系的宝贵遗产。”华民如是说。

初创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
1979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建系,成为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设立并首次倡导以国际化视角培养经济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的系科——也就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洪文达的名字,便出现在“创始团队”之中。“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的‘忘年交’,第一堂课下课,我们就成了‘烟友’。”,6年前那个阴雨绵绵的午后,在洪文达先生追思会上,作为第一届世界经济系学生,王战回忆道,“洪先生一点教授的架子都没有,气量大,心胸广,是我非常敬佩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经济改革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拓展,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从计划体制改革到原材料调拨体制变化,从流通体制放开到和邻近省市商业交流,从工业产品价格的开放到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从财政包干到企业激励机制,在实践、政策和理论上都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经济系77级朱民、世经系研究生陈伟恕和世经系79级王战三位同学计划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教研体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有计划只是个开始,真正有结果落地才会有收获。1984年,上海市高校首个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挂牌,首届中心主任便是洪文达。对于这段历史,朱民先生在“感恩复旦40年——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复旦77/78级返校大会”上的发言中,曾动情地说:
我、陈伟恕和王战三人的建议提出后,学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开了座谈会,讨论热烈,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态度,但在具体安排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会议无果而散。洪文达老师参加了会议,走到校门口,洪老师停下来,坚定地说,我们去找林克书记汇报。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老师的家中,洪老师在座,我向林克书记作了汇报。林书记仔细地听着,不停地吸烟,时时提出问题,也不时地提出新的建议。一个多小时后,当两个烟灰缸都被塞得满满时,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青年们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大事,应予支持。我们上校党委会讨论。
六周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在春寒中举行。
多年后,当年青涩尚未褪去的年轻学人,都成长为中国经济工作领域或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栋梁之才。他们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裁陈伟恕和上海社科院原院长王战等。
1985年洪文达担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系主任。两年后,兼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1990年,五市长代表团访美,朱镕基任团长,汪道涵任顾问。另有一个学者代表团随行,洪文达即在此列。朱民记得,访问期间,“他专门挤出晚餐后的时间,把我和几位复旦校友叫去,给我们讲国内的经济形势,讲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1991年开始,洪文达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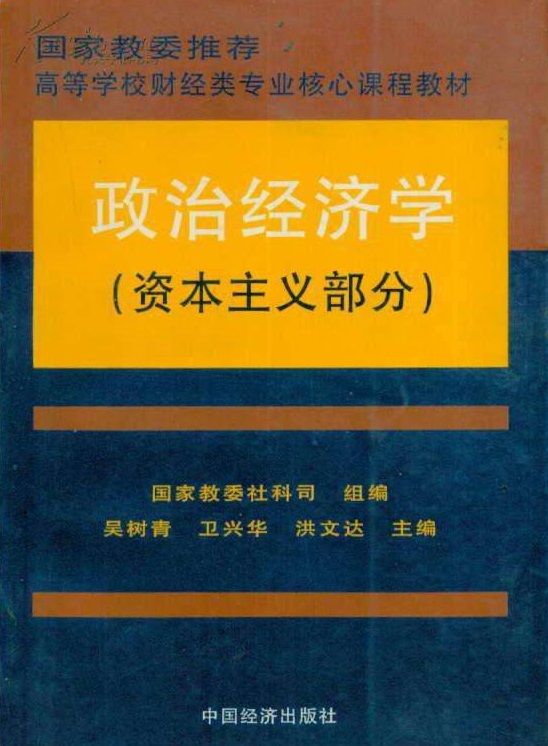
是严师,也是慈父
就像儿子记忆中的父亲永远是那个如山的男人,强永昌心里住着的洪先生,不改的是 “60几岁”的模样。直到今天,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强永昌教授依旧不敢相信,初入师门时,恩师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先生。
1992年,强永昌在财大读硕士,提前半年毕业的他想在学术上走得更远。于是,一个初夏的下午,经上海财经大学汪洪鼎教授推荐,强永昌第一次登门复旦大学第9舍宿舍,洪文达的家就在这里。敲门数下,应门声中气十足,应门者满面红光,虽着居家便装,难掩饱满精神。询问了学习、研究情况后,洪先生表示: “你的研究基础不错,国际贸易学科缺少老师,希望你可以继续国际贸易方向的研究。”
后来,强永昌就成了洪文达的学生。
洪文达爱学生是出了名的,却从不偏袒 “个人的门下”——好的机会只留给最合适的人,这大概就是一个院长的大局意识、一位大师的担当。
他是严师,更像慈父。据说当年学生张文朗远去德国做博士后,行装基本都是洪先生亲自准备的。
强永昌眼中的洪先生是一个“非常直率、原则性特别强”的人,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纯粹得近乎天真。只要是他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该做的事情,即便显得有些 “不合时宜”,他依旧会尽全力去争取。几十年来,他处事、为人的出发点都不曾改过,那就是学院的发展、学科的建设。
1982年,华民本科毕业,执教华东师范大学,后来担任副系主任。洪先生爱才,一直希望他能回到系里。可是,华师大同样爱才,事情便难免有些尴尬了。直到1990年,华民决定 “脱产”回到复旦读书,成为洪先生的 “全职”博士生。这一年,华民40岁。对于“不惑之年”的他而言,“脱产”无疑面临家庭生活的压力。于是,洪先生坐不住了。他直接跑去找校长,讲了一堆“我们要爱护人才”“引进人才不容易”之类的话。后来,华民果真以教师编制调回复旦,每学期上两门课,在职读博。 “凡是先生看准的人,抓一个就是一个,他会在各方面给你创造条件。”往事已走过整整30个年头,说到这儿,华教授的语气里仍旧装着满满的感激,“做先生的学生,对于没想法的人来说会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为他会一直逼着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他便会一直支持你。只要让他看到你解放思想、不断探索,他就会和你一起研究、共同探讨。”
作为洪先生第一个全程培养并顺利拿到学位的博士,有时上午的课结束,华民就跟着老师回家,先“混”上一顿先生亲手烧的午饭,下午便是学术交流时间,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然后再收工、回家。洪老师烧的红烧肉、响油鳝丝的味道,华民至今还记得。
洪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他爱美食,爱电影,爱音乐,爱和有想法的人聊天,除了聊经济,还可以聊文学、聊音乐。《美丽人生》《肖生克的救赎》便都是先生推荐给华民的。总之,“他是一个对于生活质量要求很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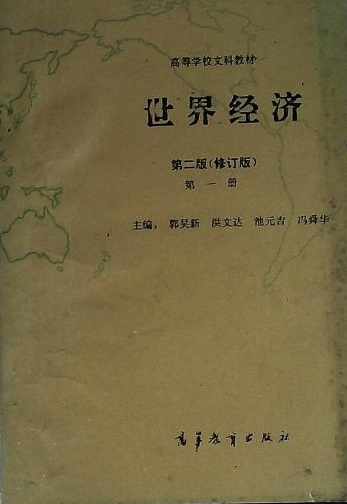
真正能够称为“师”的人,对学生的影响可以是一辈子的
事实上,对于洪老师的厨艺念念不忘的绝非华教授一个人。
那个年代,老师对学生亲切随和。朱民回忆:洪老师特别愿意和年轻人接触,虽然第一年并没有给他们上课,但他经常到学生宿舍嘘寒问暖,解疑释惑。“我喜欢听洪老师论天下时事,很快就和洪老师熟了。我后来知道,洪老师和我同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到百米。这下更方便了,周末回家,我时不时地溜到洪老师家中,听洪老师的高论,也时不时品尝洪老师的厨艺。洪老师做菜,我通常在一边打下手,他高度近视,看着他边盯着贴在墙上的菜谱,边炒着菜,还边和我说话,也真是忍俊不禁。洪老师的小儿子洪新也不时加入我们的讨论,有时我和洪老师聊完了,洪新又跟着我到我家继续我们的话题。我就这样成了洪老师家中的一员。”(朱民:感恩复旦40年——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复旦77/78级返校大会上的发言)
真正能够称为“师”的人,对学生的影响可以是一辈子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朱民在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也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几年,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准备回国。“但当时我周边的同事和家庭都不理解,当然也不支持。尤其是岳母,顾虑比较多。不说工资减少百分之九十,就说工作环境,小孩教育,就是不放心。事情就僵住了。”学生的难处,为师者最清楚,后来洪文达到美国学术访问,专程到华盛顿,住到朱民家和老太太谈心,聊家常,聊天下事。从他自己的经历,到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过程,再到未来展望,到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经过一周的努力,终于说服了老太太。洪老师回国后,朱民也收拾行李,踏上归国之路。回到上海,未及安顿行李,先去看洪老师,洪老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大声地说:“朱民,你回来就好,有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那一刻,朱民被一股暖流包裹着。当晚洪老师高兴,自告奋勇下厨,自诩技艺又有很多长进。(朱民:感恩复旦40年——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复旦77/78级返校大会上的发言)
“在复旦世界经济系,洪文达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位令所有学者尊敬的老前辈。”回想起与洪文达老师的一面之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记忆犹新。1999年,还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大四的王勇,已保送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拥有一年“自由”时光的他便四处“蹭”课。洪先生给经济学院博士生开的专题课,王勇自然不会错过。就在那唯一一次的、短暂的课间交流时间,先生还是耐心地询问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学习情况等等,并给予了更多的鼓励。从此,在王勇心中,“洪老师是一位特别愿意提携后进的师长”。小小的细节当中,洪先生对于学生的爱护可见一斑。
“洪先生对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勇说,先生提倡学生对于英文的学习,强调学生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这些对于世经系的影响,是在基因上发挥作用的。”
1990年12月18日,洪文达在《新民晚报》上撰文谈读书,他对读者说:
读书的范围要宽些,特别是搞社会科学的人。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如经济学就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关系相当密切。第二,读书当然要集中主要力量在专业方向上,但阅览广泛是很重要的。既考虑专业,又顾及兴趣爱好。总之,开卷有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养成持之以恒的读书习惯。人都是有点惰性的,只要能克服了惰性,就能学有专长。当然,读了以后,还要继之以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从读书中真正得到教益。一旦考虑某方面问题,脑子里积累的有用的信息自然会跳出来,帮助你思考和分析。
在洪文达先生看来,所谓开卷有益,就是爱好读书,从各种书中汲取营养。所谓多思,就是读书时要勤于思考,把读到的书进行消化。所谓学无止境,那就是知识无涯,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跟上形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