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创造中国现代文学新形式的圣手,他的写作,深沉博大,有一种超越文字之上的力量和温暖。他是文学家,但他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也不是谋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
几乎每隔数年,我们都会隆重集会,纪念鲁迅先生,像面对所有尊敬的长辈那样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思念。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又一次向鲁迅先生,表达敬意,诉说我们这些年来自己的所思所想。
鲁迅先生诞生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文化奇迹。此前没有这样的人物,此后也很少有了,他的同时代人中,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他与他们并肩协作,创造了中国新文学的辉煌业绩。但他与他们又不一样,鲁迅先生没有像他的很多文坛朋友那样见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经历此后的风云岁月。但他55岁的生命流程,在中国文学领域铸就了最坚强灿烂的文学坐标。如果说其他先生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像激流,像浪花,那么,鲁迅先生更像是激流险滩中的中流砥柱。他坚强有力,无所畏惧,面对狂风恶浪,从不退缩。他像高山峡谷,引导着中国文学的大江大河,千转百回,流向大海;他像星辰,给那些至暗时刻寻求援助的广大读者以信心和希望,他像大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他的写作,深沉博大,有一种超越文字之上的力量和温暖。他是作家,是文人,是创造中国现代文学新形式的圣手,但人们喜欢称他为“大先生”。所谓大者,“得其大者而兼其小”。他有巨大的胸怀。早年“走异路,逃异地”,脱离了江南小镇的狭小天地,告别了“读书应举”的传统道路,赴金陵求学,后东渡日本学医。一路走来,他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人生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他遇到了章太炎、藤野先生这样的精神导师,结交了许寿裳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学,回国后,他加入《新青年》阵营,发表《狂人日记》,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由此在文学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是文学家,但他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也不是谋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他说自己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批判毫不留情,尽显文学家的敏感和现代眼光。像《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变态心理的描写,像《祝福》中对祥林嫂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变故后的神态的捕捉,像《故乡》中对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对照,像《孔乙己》中对跌入社会底层的读书人的同情和悲哀,这些文学上的探索都显示出鲁迅在社会批判上的自觉意识。这不仅构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强大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亮点,也大大提升了新文学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影响。在鲁迅作品的影响下,小说不再是“雕虫小技”,人们也不再把“小说”当作“闲书”,而是视为人生的教科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值得人们花费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伟大事业。
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个风雨飘摇、万马齐喑的旧中国,竟会横空出世,诞生像鲁迅这样举世无双、影响深远的文化巨匠。这是令很多人赞叹不已的现代文化奇观,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值得骄傲的地方。1937年10月,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公学发表演讲,他将鲁迅与孔子相比拟,称颂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看得远,看得真”,有政治上的远见、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像战士那样的牺牲精神,这三大特点构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精神”。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鲁迅,将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有关“鲁迅精神”和“鲁迅方向”的提法,几乎成为评价鲁迅的定论,影响着此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引用鲁迅的话,并赞同“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提法。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茅盾等当年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文学巨匠,在纪念鲁迅的各种会议上,都强调“鲁迅方向”的重要性,从各方面阐释和丰富“鲁迅精神”,不断赋予“鲁迅精神”、“鲁迅方向”以时代内涵。1981年9月,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周扬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讲话。他强调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是大变革时代产生出来的,是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代,鲁迅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呼唤,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重读鲁迅与思考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问题紧紧地联系起来。

鲁迅的话题,总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想内容。1980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筹备大会上,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人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在《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纪念鲁迅》的讲话中,他认为纪念鲁迅构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现象,我们时常怀念鲁迅,不断强调鲁迅精神,但我们拿出来的研究成果是否能与鲁迅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地位相匹配呢?他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希望鲁迅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一点,研究的方法更科学严谨一些,不要把鲁迅与时代割裂,不要把鲁迅与同时代人割裂,不要把鲁迅的文学事业视为到鲁迅为止就终止了。他认为鲁迅留下了许多难以企及的成就,但“所谓难以企及,不是说不可以企及,也不是说不可以逾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就要得到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鲁迅自己就不这样看。”
事实上,在学习、研究鲁迅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出版的赵景深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旁证》,丰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材料,从而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小说史研究推进了一步。王元化先生对鲁迅的思考,贯穿了他晚年的思想,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鲁迅与太炎》、《再谈鲁迅与太炎》、《鲁迅与周作人》、《鲁迅的曲折历程》等,从思想史、文学史角度,梳理了鲁迅思想的来源,包含了很多理论新见。钱谷融先生在《谈<伤逝>》中,对鲁迅小说《伤逝》的文本解读,有新的体会和感受。《收获》杂志发表冯骥才、章培恒先生围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而展开的辩驳文章,激发新世纪文学爱好者对鲁迅的反传统态度重新评价。
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新世纪以来展演过不少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如肢体剧《铸剑》和波兰导演陆帕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狂人日记》。在语文教学上,鲁迅作品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语文教育,尽管选录鲁迅作品多少问题,曾在语文教育领域引发讨论,但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来说,鲁迅的名字并不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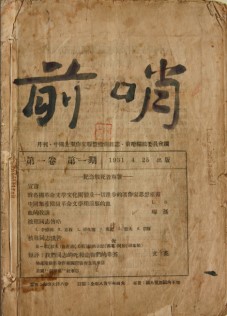
鲁迅先生批判过“国民性”,但这种批判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而是思想上的扬弃和自我更新。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始终充满自信,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始终抱有热忱。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文章中,鲁迅不仅对中国人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予以礼赞,更对“中国脊梁”充满自信和希望。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鲁迅精神和鲁迅传统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到鲁迅纪念馆参观访问,担任总书记后,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和多种重要会议的讲话中,引用鲁迅的作品。最近这些年,对鲁迅等现代作家的宣传,较之以往有所加强,特别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入选数量,有了保证。因此,在今天这个海量信息四处漫溢的世界里,鲁迅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我们因为接近鲁迅而感到精神充实,因为阅读鲁迅而感到文学的有力。
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我们有很多话想跟鲁迅先生说,有很多感触,想跟鲁迅先生交流。我想这应该就是鲁迅的精神魅力所在吧。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作者:杨扬
策划:王雪瑛
编辑:王筱丽
责任编辑:王雪瑛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