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深翻译家郝运先生于2019年6月10日下午在仁济医院西院逝世,享年94岁。
郝运,原名郝连栋,法国文学翻译家。1925年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河北省大成县(现为天津市静海区)。民进会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青少年时代在国难当头、战乱频仍中度过,先后在南京、重庆、昆明求学。1946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1947年任职于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月刊》。
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平明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8年春因肺病复发,向出版社提请辞职获准,病愈后专职从事法国文学翻译,翻译生涯达七十年。译出《红与黑》《巴马修道院》《黑郁金香》《都德小说选》及合译《三个火枪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等六十多种法国文学名著。2002年获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中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5年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16年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颁发的 “2015年度上海文艺家荣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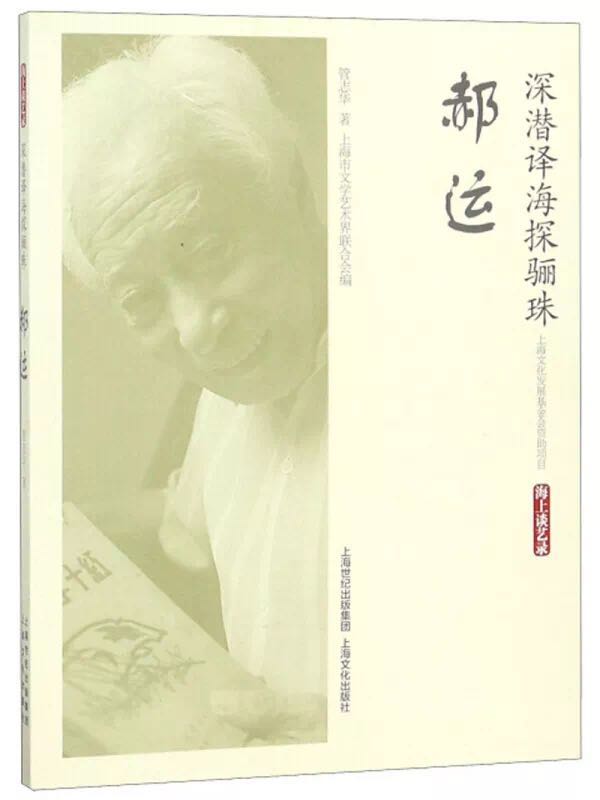
2018年底,上海市文联主持的“海上谈艺录”丛书之《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出版。作家管志华在撰写此书时,曾多次专访郝运先生。在访谈过程中,管志华深感郝老的谦和、低调,“身为沪上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三位大家之一, 从来不讲自己的翻译特色如何如何,对前辈、同行的译著却是推崇有加。”郝老的为人风范让人感动,他在翻译领域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思考。
特此刊出这段访谈,以志缅怀。
管志华(以下简称管):您是如何抉择外国作家作品的?是不是在作家本国发行量大的,就拿来翻译?还是说,要考察该作品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和本身的艺术成就等?

《红与黑》(精装本)〔法〕司汤达著 郝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郝运(以下简称郝):从译者的角度来说,选择好外国作品,是很重要的,不能随随便便选。我想,倒也不是凡是在作家本国发行量大的,就要拿来翻译。太功利性了不行,不能太短视,不能唯发行量是吧?这不符合文艺史的发展逻辑。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最公正的。譬如,1830年11月,司汤达《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后,在毗邻的德国立刻引起文学巨匠歌德的注目,年逾八旬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司汤达的这部小说在俄罗斯也有它的知音,出生于1820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亲近之感”。可当初《红与黑》出版后,在本国受到冷遇,初版仅印了750册,后来根据合同勉强加印几百册,纸型便束之高阁。他一生写了33部著作,只出版了14部。虽然如此,司汤达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充满信心,他大胆预测:将“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历史兑现了他的预言。自司汤达 “被发现”后,亦即渐渐被公众接受后,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司汤达的一些杰作,开始不胫而走,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评判作品,要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中外都一样。一部优秀小说,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还是以《红与黑》为例,1828年初,司汤达对一桩刑事案件报道产生浓厚兴趣,进行文学想象和艺术创作,构成了小说的基干,成为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风俗画。除了描述主人公于连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与矛盾心理,更将他和德·雷纳尔夫人、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故事贯穿整个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有力鞭挞,对平等自由的恋爱和婚烟的大胆肯定。同时,一部优秀小说总是极富艺术特色。光有思想内容不够,还须艺术化地表现这些内容才行。这需要在艺术创造上具备特色。如果说巴尔扎克感兴趣的是造成一个人的“境遇”,那么司汤达则倾心于“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开创心理小说之先河。仔细鉴赏《红与黑》,读一读其中好多地方的心理描写,读者会获得莫大的艺术享受。作为翻译家,我们要体悟作家原著的艺术特点,用力气在翻译过程中将它反映出来。文学技法没有一定之规,文学名家总是各显其能、各尽其妙,翻译家要善于体悟其妙,进行再创作。

郝运翻阅《红十字史话》
管:郝先生,您一辈子与翻译打交道,与文字为伍,译了六十多部书,绝大部分都是法国文学名著,您能否谈谈对法国文学的印象?
郝: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源远流长,光照人间。自中世纪开始,流派纷繁,名家巨匠层出不穷,佳作名著浩如烟海。作为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我只不过翻译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法国大作家,即司汤达、法朗士、大仲马、莫泊桑、都德的一些作品,可谓大海滴水、吉光片羽。我对这些大作家的作品是有所偏爱的,甚至会边翻译边赞叹——像司汤达的文章风格朴实、明晰、严谨,长于心理分析,文笔冷静,语言不多装饰,不追求美艳造作的文风,却又令读者时时会随之感动、共鸣;莫泊桑的小说大都以日常生活为背景,平淡却精准得像实际生活一样,没有人工的编排与臆造的戏剧性,不以惊心动魄的开端或令人拍案叫奇的收煞取胜,而是以真实自然的叙述与描写吸引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翻译也该是如此,关键是要深入到原著者的内心,跟着他们塑造的人物不断转变自身角色,就像演员一上台就得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戏中的人物角色性格,而导演则要把握整部戏的各种人物性格,所以,翻译好一部书,译者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将自己的情感、个性“移植”,尽可能不走样、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管:确实,优秀的译著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些优秀作品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说句玩笑话,这些法国大作家得好好感谢您这位中国知音,正因为有了您的出色翻译,他们的经典之作成为中国读者的心爱之物,从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走向千家万户。对此,您的感觉如何?

年轻读者写给郝运的信
郝:当然我高兴呀,因为中国与世界相连,中国读者能读到外国文学经典,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有益于中华文化汲取养分,丰富发展。翻译就是发现美的过程,译者与读者都乐享其中。而中华博大的文化同样需要传递给世界,所以,作为中国翻译家要有使命感,进行“双向传递”。文学翻译其实也是再创作。这方面,我不过是个“翻译匠”,对“翻译家”头衔实在不敢当,唯一愿望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好翻译。
管:说到“翻译匠”,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四个字。郝老,您的艺术道路,体现的就是这种不断自我加压、不断进取的精神。您以毕生心血,为我们年轻读者造福,也是树立了精神榜样。由此,您的精神乃至译作也就特别受到瞩目。我们就该向您学习,把这四个字融会贯通,在工作上凸显 “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打造新时代中国人的一种全新内在素质,摈弃松弛懈怠、马马虎虎的工作状态。这样,我们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就会快速推进,奔向光明的未来!
郝:你说得太好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文化也要及时跟上,甚至引领,我老了,再也做不了多少事,希望中国的未来更美好。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不高的。有个成语:探骊得珠。文学翻译要做好,就似“探骊得珠”,是很难的。一个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翻译工作者必定是要自我加压,要为读者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反躬自问,自己究竟做得怎么样?平心而论,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感到是努力做了,但做得还很不够。很多前辈,很多同行,他们的工作值得我赞美、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就是向人家学习,取人长补己短,一路这样走过来的。自然,翻译的艺术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翻译作品丰富起来了,出现各种评价,各种争议,也正常啊。总体上说,评价翻译作品,要客观、公允,要看到其中的长处和短处,防止片面地褒扬或贬低,不要走极端,这是我的观点。
管: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关注中国,语言交流、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郝运与妻子童秀玉在书房
郝:即便如此,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翻译家,世界文学将会留下一段空白,毕竟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样样语言都学到精通。没有翻译家,即使我们像伟大的歌德那样,信心百倍地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到来,可是语言障碍的高山挡在面前,我们还是看不到山那边的无限风光。所以,中国的翻译事业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为人民、为读者献上优秀的外国文学译著,希望翻译界人才辈出、人才济济,兴旺中国的翻译事业。同时亦希望从事这行当的后起之秀能静得下心,不求大红大紫,但求温和清静,既不抱怨,也不摆功,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乏功。人生难得是心安,心安人才静。这是我的希望,更是期待!
郝运老师,一路走好!
永远怀念您!
来源:上海文联
作者:管志华
摄影:陈焕联
编辑:姜方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