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向西藏路桥北的残敌冲击
指挥上海战役的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大家都叫他陈老总。他在部署上海战役时说:解放上海“就像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一级一级传下来,不用多作解释,大家就明白,就是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使大上海的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尽量不受损失。当时还提出“让大炮休息,让炸药靠边”,在进攻市区时,要求主要使用轻武器,不准开炮、用炸药。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当时称淞沪战役)打响。我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9和第10兵团,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
经过10天外围作战,我军攻占了守军的外围阵地和部分主阵地。……5月25日凌晨,我们团和237团包围了国际饭店,控制了跑马场(今人民广场)一带。国际饭店内的敌人投降后,我进入国际饭店,与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同志取得了联系。接着,在团统一指挥下,我们三营向苏州河北岸攻击。我们七连在最前面,接近苏州河南岸垃圾桥(西藏路桥)时,遭到居高临下的敌人火力封锁,我们七连进行了四次冲击,都未成功。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国民党军占据的一幢小楼上往外喷着火舌,对我们威胁很大。我和萧连长商量,确定先夺取小楼。我们叫来操纵掷弹筒的孙茂礼,对他说: “你瞧好了,楼顶上有敌人的工事,楼下住的是老百姓,只准你打楼顶,不许打到楼下。把你的看家本事拿出来吧!”
22岁的孙茂礼是学徒工出身,入伍后8次立功,在战斗中练就一身过硬的射击本领,被战士们称为“神炮手”。只见他沉着地瞄准小楼顶上的工事,几发掷弹筒,把国民党兵打得晕头转向,顿时乱成一团,重机枪成了哑巴。我带一个排趁机冲进小楼,在“缴枪不杀,投降优待,抵抗死路一条”的喊声下,据守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全部投降。
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沿河边拉上铁丝网,用麻袋装上沙子,甚至用面粉袋等构筑工事,形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敌人依托高大楼房上的火力,封锁我军过河必经的马路和桥梁。我军多次攻击无效,遭敌人火力严重杀伤。我们对面的敌青年军第204师,自诩为“党国中坚”,占据着坚固高大的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大楼负隅顽抗。
当我们7连往桥上冲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像雨点般地扫来,我最要好的抗大同学张昆被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大家心情都很激动,但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军党委决定不能使用火炮,部队被拦堵在南岸,真是心急如焚。
我焦躁地在地上转圈苦苦思索,无意中踩到一个下水道井盖,我从前没有见过这东西,问房东这是干什么用 的?房东说是下水井,雨水、刷锅洗碗的水都从这里流下去,顺着排到苏州河和黄浦江。我想:“能不能从这里钻到苏州河?”房东摇头说:“不行,不行,里边都是脏水,臭得很。”我告诉连长,让他掌握连队,我去探探路。我揭开下水井盖,找了个竹竿,探下身子一搅,顿时臭味冲鼻,苍蝇、蚊子乱飞。
我正要跳入下水井时,通讯员张瑞林一把拽住我说:“指导员,你不能先下去,我来。”说着他抢先跳了下去。他说:“往北看有一个大洞,猫着腰可以过去,就是臭得受不了。”我下去以后,排长王其鹏紧跟着也钻了下去。这个下水井实际上是一条通往苏州河的排水沟,人可猫腰通过。里面一团漆黑, 污水熏得人简直要昏过去。十几分钟后,我们高兴地从排水道口钻出来一看, 是苏州河。苏州河水很脏,水已没过了胸脯,深的地方能没过头顶。
看到对岸国民 党军哨兵的影子在晃动,我小声告诫王其鹏和张瑞林:“不要弄出响声。”好在苏州河的流水声掩护了我们的行动,敌人的哨兵对水面上的动静看不大清楚,而我们从水面看岸上却十分清楚。
我们三人偷渡到河对岸后,互相一瞅,身上脸上都是污泥,但哪还顾得上这些,只管猫腰顺斜坡而上,悄然向前摸去。
到了大桥的左侧,见旁边有一排房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我们向后边绕去。这时,天下起了小雨。看到一个国民党军哨兵缩着脖子在房外溜达,我想先逮一个“舌头”,就对张瑞林和王其鹏说:“你们看我的手势,他往那边溜的时候你们趴到这边,等到他回头,就把他按倒。”张瑞林和王其鹏配合默契,冷不防一下子就把哨兵撂倒了,然后把他推到一扇门里边。
我们三人全身都是黑乎乎的,只有牙齿是白的,这个哨兵还以为遇上了什么鬼怪,吓得上牙打着下牙,浑身哆嗦。我对他说:“你老实点。我们是解放军,不杀俘虏。你不要喊叫,听我们的命令,快带我们到指挥部 去。” 盘问后,我们塞住这个哨兵的嘴,由王其鹏和张瑞林扭着他的胳膊,我举着枪走在前头,蹑手蹑脚地进了大楼。
哨兵带着我们进了电梯,我们三人 都是第一次坐电梯,电梯一动很紧张。张瑞林用枪抵着哨兵的脑袋说:“你这个坏蛋,想把我们弄到哪儿去?”那哨兵吓得“唔”“唔”地直摇头。我说:“不要慌,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哨兵面对着三支枪口,战战兢兢地把电梯开到了四楼。
一出电梯,就有一个声音传来:“谁啊,干什么的?”我一看,是个国民党兵,一个箭步扑上去,缴了他的枪。三人押着两个俘虏,往右一拐,到了一个大房间的门口。
借着幽暗的灯光,我往里一瞧,看见里面横七竖八地坐满了抽烟聊天的 国民党兵。我不禁一愣:敌众我寡,如何是好?也来不及多想,我纵身跃入室内,举起驳壳枪,大声喝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机智聪明的王、 张两人也马上举枪呼应,大壮声势。
室内本来就灯光昏暗,加上“瘾君子” 们吞云吐雾,整个屋子弄得乌烟瘴气,国民党兵眼见门口三条黑汉骤然降临, 吓得魂飞魄散,个个哆嗦得像筛糠,有的竟哭爹叫娘,乱作一 团。
“闹什么,来了哪个奶奶的熊?”突然间从里屋传出声音。话音未落,出 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得醉醺醺的,歪戴着帽子,大敞着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张瑞林眼疾手快,冲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不许动, 把手举起来!”这军官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酒倒是吓醒了一半,连连打着嗝儿,颤颤抖抖地举起了双手。 我看清了这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当即缴了他的枪,并用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厉声喝道:“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现在快下命令,叫你的兄弟们放下武器,否则,我先毙了你!”
接着,我大声说:“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解放军已经进了上海。这大楼也被占领了,我们的部队正在上来,只有缴枪投降,才是你们的活路!” 王、张两人也大声喊道:“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国民党兵的意志顷刻瓦解,不等那上校下令,房间内已响起一片哗哗啦啦丢枪落地的声音。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朝张瑞林使了个眼色,大声说道:“你快下去通知部队,说这里的弟兄们都已放下武器,不用上来啦。”
“是!”张瑞林马上会意,押着两个俘虏下楼去了。王其鹏也心领神会, 上前扭住那个上校军官。满屋的国民党兵就像无头之蛇动弹不得。我转身命令上校:“你愣在这里干什么?快下命令,让你的部队放下武器投降!把桥上的人撤下 来。”
王其鹏用枪狠狠地戳了戳那上校的脑袋:“再不讲,我要了你的狗命!”国民党上校军官无可奈何,只得拿起电话筒……在苏州河南岸,正在布置下一次冲锋的萧连长发现对面的国民党兵纷纷后撤,又不见了我和王其鹏、张瑞林,已经明白大概,立即带连队跃过苏州河,肃清了附近的国民党 兵。
聂凤智军长听说我们三个人不费一枪一弹,抓获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上校副师长,迫使其师部及三个营放下武器,对我们团领导说:“把这个迟浩田找来,我看看他长得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竟能制服一千多敌人!”在愚园路军指挥部,聂军长握住我的手,端详良久后哈哈大笑:“噢,原来你没有三头六臂呀!头倒长得不小!”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是山东黄县人,和我们招远县相邻,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老乡,我看你可以改个名字,叫迟大胆吧!” 聂军长和其他首长都笑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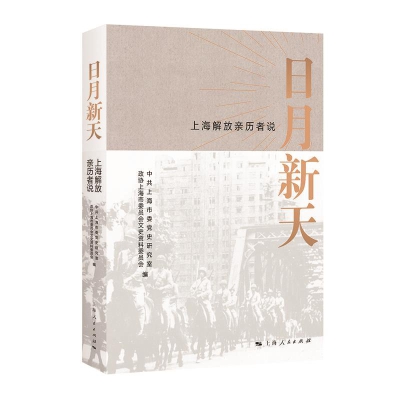
节选自《上海战役亲历记》一文
摘自《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一书
作者:迟浩田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出版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