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1942年出生于美国的约翰·欧文(John Irving),是当代文坛无可争议的小说宗师、杰出编剧,1999年他以《苹果酒屋的规则》拿下奥斯卡金像奖改编剧本奖。村上春树奉他为偶像、男神。约翰·欧文的代表作有《独居的一年》《 盖普眼中的世界》《马戏团之子》等。而新近引进出版的《新罕布什尔旅馆》被誉为“欧文最好的作品”,被译为35种语言畅销40多个国家,同名影片由奥斯卡影后、《沉默的羔羊》女主角朱迪·福斯特主演。
《新罕布什尔旅馆》讲述了一个快乐又悲伤、疯狂而又充满宿命感的家族史,堪称美国版《活着》,小说版《布达佩斯大饭店》,看看中国作家张大春如何解读这部作品:
你读小说吗?
对于一位已经捧起一本小说的读者而言,这是个多余且没什么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说法:你玩拼图吗?
早在1762年,一位英国的印染工史匹兹百瑞(John Spilsbury)发明了一种在当时被称为“解剖地图”的教具,它是一张黏贴在木板上的黑白板画地图,成形之后复以细线锯手工切割成不规则的小块,再经组合,便看似恢复原画旧观,而认识了一幅地图上各个地点或区域的相关位置。19世纪以后,彩色石板印刷术的发明和印模切割压力机的细致发展使得这项工艺逐渐有了大规模的市场前景。拼图板终于成为一种风行全球的游戏,童叟咸宜。
玩过拼图的人都知道:把一堆数以百计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是一桩耗时费神,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无实利可图的勾当。经过几个乃至几十个小时穷尽目力的搜拣、拼合之后——倘若制造厂商竟无丁点错讹遗漏——面对一张看似与参考图(原画)差堪一致、却爬满了曲线锯(jigsaw)迤逦歪斜的切割纹的图板,得意中仍不免神伤,总依稀感觉那切割纹略有几分碍眼(若无这等纹路,岂不端的是一张光滑平整的原画?)——然而玩家的小小怅憾实可以转瞬即逝;试想:一张光滑平整的复制画能有什么意趣呢?正是那不容毫厘之差的切割纹在帮助着玩家重建一座拆碎了的七宝楼台,也正是那切割纹摧残破毁的轨迹见证了玩家还原一幅所谓原画的苦心孤诣,不是吗?
似乎没有人能用任何科学工具或方法证明近代小说在叙事技术上的发展和拼图板游戏的改良和普及有什么关联——那是神秘主义论者和妄想家可以努力勾稽穿凿的题目。不过,我总在浪漫主义时期(姑且浮掠地以18世纪末标示出一条准切割纹的虚线)以后的小说里找到更多,且逐时益多的拼图游戏的趣味。
撇开作品所展示的意识、思想等课题不说,但就铺陈手段而言,19世纪以来的小说家显然较他们伟大的前辈——塞万提斯或拉伯雷、笛福或斯威夫特——更重视一部小说前后文如何呼应的问题。倘若将拼图板上的切割纹想象成时间,小说读者据以进入并重塑角色处境或故事氛围的利器则端赖于作者如何精确地掌握读者逐字逐句而下之际所保有的细节记忆,且在适当的时机唤起那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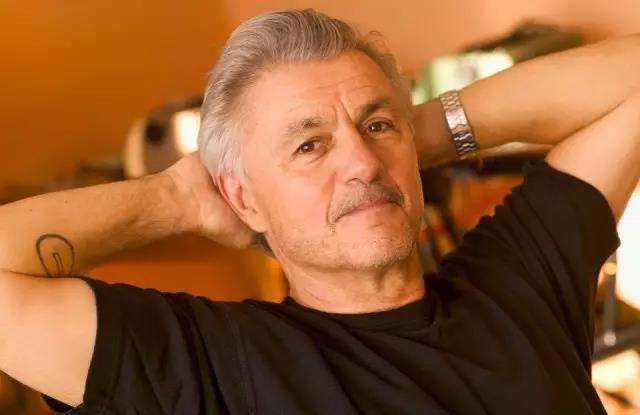
我们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那里一定早已见识过这种本领;从来没玩过拼图的中国近代方言小说家韩邦庆也在论及他的《海上花》时用“穿插藏内”四字轻轻揭露了小说布局的要诀。一个熟练的小说家不会设计一块只有皑皑白雪或渺渺蓝天的拼图板,他必须和读者的记忆力捉迷藏;这是现代小说家艰难的宿命。
我在读过几本约翰·欧文的小说之后才不期然从年轻的欧文迷兼翻译者徐寯口中得知一个似乎已属文学人口常识的背景:欧文曾经有过读字困难(dyslexia)的问题。读字困难较常出现于使用字母书写系统的地区,它究竟是一种心理或神经性的病变与否仍是一大争议,成因究竟是脑部伤害、遗传性异常抑或拙劣的教学环境所造成……亦莫衷一是。令我于惊愕之余而别有体会的倒不是欧文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成为杰出小说家的“奋斗历程”,却是他表现在小说上的特殊机巧。
欧文出生前180年,同名为约翰的印染工史匹兹百瑞发明“解剖地图”。在那个时代,一幅锯碎了的地图的零散片段并非毫无指涉的色块;如何分割一幅完整的地图显然要煞费设计者的脑筋——他必须假设:重构这地图的人(年轻的地理课学生)所能凭借的一则是粗略的舆地概念(如:某城在某城之东、某河在某山之北),一则是细线锯切割之后的木板边线如何相互吻合的空间感。当其中之一不敷应用之际,另者则或可为之救济。
小说却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构成小说的元素复杂得多之故。尤其是当小说家试图处理较多的角色、较繁复的场景、较长跨幅的时间以及较曲折变化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层次之际,布局的诸般考量不可避免地成为最主要的设计。
小说家应该知道——起码他要有推测度量的能力——在历经大约多少篇幅之后,他的读者还会记得某一曾经出现的元素。在读者方面而言,一般的阅读习惯总不外是这样的:我们追随着叙事者的目光或主人翁的脚步,念兹在兹的是逐字逐行所编织起来的一幕幕呈现故事的时空;除非极其孤拐的特例,没有人一面读小说、一面主动打断自己、刻意去回想在多少章、多少页之前,作者曾经写了些什么。换言之:读者的义务原本就是逼取那逐字逐行的当下,在这个过程中,他有随读随忘的权利。
至于小说家——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则艰苦得多,他在安置每一个小说元素的时候都不免要凭敏锐的直觉或熟巧的训练去判断:这个元素能撑得住、经得起多少篇幅的叙述的冲洗,而仍能唤起读者的记忆?
《新罕布什尔旅馆》
[美]约翰·欧文 著 徐寯 译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比方说:欧文在《新罕布什尔旅馆》的开篇即如此写道:“父亲买熊那年夏天,我们都还没出生”——一个多么故作轻描淡写之笔的强烈意象迫使我们读下去(为什么有人会去买一头熊?他怎么养那头熊?那真是一头熊吗?),欧文一定知道我们怀里这些问题的困扰程度也许不亚于买下一头熊的父亲;但是他不急,他知道“父亲买熊”的严重性足以撑持一段时间,让他把父亲和母亲平凡的爱情、平凡的家世、平凡的小镇生活略事点染,当我们历经将近六千字的旅程、读到“一阵引擎声盖过了乐团的演奏,许多正在跳舞的人纷纷离开舞池,出去看个究竟”之时,没有谁还记得“父亲买熊”——不过欧文了解:这暂时性的失忆并非疾病,而是小说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之最不可或缺的一种欣赏能力。唯其读者在逐字逐行、且站且走的旅程中能随时忘却那些即使令人惊愕不已的强烈意象,才能够在重新被小说家唤起记忆之际得到快感——方才那一阵引擎声来自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犹太驯兽师所骑乘的印第安摩托车,车边附有侧座。当弗洛伊德一边说着话,“一边解下侧座的帆布篷”的时候,读者不期而然读到下面这个句子:“熊就坐在里头”。
较诸他心仪的前辈狄更斯,欧文更绵密、大胆地运用这种岔题、插叙的手法编就一种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大师们所无从想象的“乱针绣”般的布局,让一个繁琐复杂的现代世界有了属于它独有的叙事风格。我们没有足够的医学(科学)证据可以认定这种艺术手法出于欧文个人那神秘的病症使然,但是毋庸置疑地:欧文比他同时代(及稍早)的绝大部分知名的英美世界的小说家更注重(甚至可以用“牵挂”二字来形容)小说中某一元素如何衔接起另一元素、某一主题如何过渡到另一主题、某一情节如何转折于另一情节的技术。

一旦和纯粹而沉重的康拉德、浓烈而幽微的福克纳、锐利而絮叨的贝娄或佻达而炫奇的罗斯相较起来,欧文的小说总能在更多浪漫传奇式的悬疑和惊奇的交织之下让读者往复穿梭于倍胜于这些大师们所点染或镂刻的现实。说得具体一点:欧文对读者的记忆力有着更深的焦虑——他不知道读者在历经冗长的情景铺陈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转折之后是否还能被唤起有关前文所穿插藏内的元素的印象。他不敢冒这个险;更不敢要求所有的读者像一个有读字困难问题的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辨识小说“说过些什么”和“正在说什么”以及“从什么说到什么”。于是欧文益发紧凑地压缩文本,务使每一页都饱含着前此(或后此)数页之内可以相互“声援”的元素。
随时呼应文本结构的叙述手法并非没有危险——它很可能让一个单薄的故事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令读者感觉复沓;但是欧文总有办法找到一种离题(digression)的方式使前后文之间产生鲜明的张力。比方说:《苹果酒屋的规则》第五章开头掉笔描述圣克劳斯火车站长的十一个段落,乍读起来,似与上文风马牛不相及,直到第十二段的“看见勒奇医生与荷马庞大的身影”、乃至“听见‘巫师!’两个字”时,读者才不免身历其境地体会到火车站长该有多么“惊惧疑惑”——毋怪乎这可怜的“宗教邮件受害者”会给吓死,读者难道不也受那离题之文的牵引而在发现真相的当儿感受到迫人的意外和荒谬吗?
有些时候——为了让上下文锻接得更为流畅——欧文也会使用一些省力的工具:让小说的角色摊派一部分叙述的任务。《盖普眼中的世界》里的盖普和《苹果酒屋的规则》里的勒奇医生显然是欧文最得力的助手,这种担任“第二声部”的叙事者非但增加了布局的自由度,使原本难以拼合的段落有了溶接的榫头,也常替不方便现身说法的作者发挥许多难已透过情节或对话展示的雄辩——有意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却深恐“选错了叙事观点”(多么可怕的现代小说禁忌?)的人士不妨仔细钻玩欧文如何利用“第二声部”折冲樽俎的手法,以及设若抽离了“第二声部”的话又将如何磨损小说的流畅程度。
我的另一个建议是:倘或再对照那部《咆哮山庄》,作者艾密莉·勃朗特从头到尾都没打定主意该让谁说这个不知该属于谁的故事——则更能细腻地体会:当欧文扩充了布局的自由度之后,小说的秩序感和结构性并未相对减弱(它顶多让小说的篇帙变得长一些),反而在更大的尺幅上显示了小说元素有更多相互呼应的可能。毕竟,一块由2000个碎片组合而成的拼图板不应该比一块由350个碎片组合而成的拼图板更松垮——它只不过是一项较耗时也较有趣的追踪旅行而已。
玩拼图的人从不在乎旁观者取笑其所为者竟属“无益之戏”,他们只担心拼到末了少了一两片零件。读欧文小说的人则非徒不必如此担心;掩卷之时,想必还能够深深回味那精巧布局之中所洋溢着的幽默、知识和温暖。
作者:张大春(作家 书法家)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