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底,由陕西籍作家陈彦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装台》,在央视一套赢得收视和口碑双赢,自己替别人装台,别人给自己装台,人们相互搭台,共同成就舞台……一时间, “我们都是装台人”成了共同的心声。
从“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到舞台系列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从戏剧、电视剧、歌词、散文到小说创作,陈彦获奖无数: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飞天奖……他同时也时刻保持清醒:奖项只是创作的副产品,文学艺术不能奔着获奖去创作,急功近利是创作的大忌。
在陈彦的作品中,能清晰地闻到一股浓浓的生命烟火气息。他一直坚持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写底层生命状态、点亮普通人物身上的价值光芒。
对于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他烂熟于心。“写熟悉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写不熟悉的东西,总会挣挣巴巴的,这时难免会用一些‘技巧’来弥补生活的不足。”陈彦说。
几乎是在《装台》热播的同时,他的最新力作——“舞台三部曲”第三部的《喜剧》已由《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前后发表,作家出版社推出。
近日,本报记者就“生活与创作”这个话题对陈彦进行了采访。

山里娃的幸福,
是挤在电影银幕后面反着看也很美
从商洛镇安、到省城西安,再到首都北京,陈彦的工作单位、职务一直在变,“我这一生都在不停地换地方,唯有创作,是一直坚守的阵地。”
秦岭南麓,有一座名叫镇安的美丽小城,峰峦叠翠,山清水秀。
那是陈彦梦开始的地方。
1963年,他于此地出生,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是人民教师。
小时候留存至今的记忆,基本就是在大山里穿梭的日子。由于父亲每隔几年就要换工作地点,孩提时代的陈彦就跟着父亲搬来搬去。
镇安曾是个闭塞之地。过去,遇到雨雪天,早上六点乘车从县城出发,可能半夜才到西安,这样的交通条件注定了“山里人”生活的艰辛。
父亲和雇来帮着搬家的村民轮流牵着陈彦,携一程、背一程、“架马夹”驮一程,陈彦就是这样记忆着大山的风景、记忆着厚道的山民,并在他们的背上安然入睡。
质朴、憨厚、少言,是山里人留给陈彦最深的记忆。
后来,上学时“勤工俭学”,在生产队里一住就是几周,吃大锅饭、睡大通铺,割麦子、点洋芋……他也都干过。在山里最幸福的生活,就是结伴赶几十里地看一场电影,即使挤在银幕后面反着看也很美。为看县剧团的戏,他和小伙伴们撵了三个场子,冬天还掉到河里了,一只棉鞋再没捞上来,但依然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一个作家会写什么样的内容,一定与他的生活有关联。童年记忆对陈彦的影响巨大。对山里人的感情,对电影和戏剧的记忆,让陈彦一直努力在创作中聚焦他们。
“我本身就是山里人啊!”陈彦说。
时代的前行,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投入了创作的怀抱。改革开放后,创作成了镇安年轻人的时尚,几乎每个青年都有一个文学梦。陈彦也成为追梦人的一员,17岁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随后又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发了散文,激动得一天到街上转三圈,看别人都是啥反应。
除了创作,他还从未有过其他的职业规划,父母对他的决定特别支持。“在那个‘全民经商’还没到来的时代,山里人对功利性的商品观念还是抵制的。当你在读书、学习,父母就认为这是在做正事。做正事就该支持。”陈彦说。
陈彦的阅读习惯,也是在镇安养成的。他从少儿时代起,就迷上了阅读,印象中看的第一本比较“大”的书是《高玉宝》,那时才十岁左右。投身文学创作后,他读得越来越“疯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雨果……阅读量非常大。在县城工作时,他所在宿舍床上靠墙位置摞着半人高的书,人睡一半,书睡一半。读每一本,上面都标满了不认识字的拼音,还有“眉批”。
“写戏就只读剧本,写小说就只读文学,可能与想发财就去读《发家指南》,想炒股就去读《天下股神》,想应聘就去读《老板您好》的效果差不多。如果阅读只是想找到一种解答和对应,要求立竿见影,这是很危险的。”陈彦说,“阅读是寻求营养,兴趣越宽泛越好。”
“开疆拓土”地阅读是陈彦创作的基石之一。

任何生活都有意义,
就看作家如何“感光”
陈彦与戏剧结缘,则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时陕西省教育厅和文化厅要组织“学校剧”评奖,县文化局领导让陈彦写个戏去“搪差”,他就写了一个九幕话剧《她在他们中间》,讲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和一群中学生之间的故事。让陈彦惊喜的是,五个月后,话剧获得全省评比二等奖。
这给了他巨大的激励,他一头扎进了戏剧的海洋中,22岁那年,一口气连写了四个剧本,并且都获得排演机会,一下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
在25岁这个无限美好的年纪,陈彦被调入省城,成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业编剧,一做就是七年。
三十出头的那几年,陈彦特别“高产”。舞台剧之外,他涉足电视剧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得了“飞天奖”。此外,他还为几十部影视作品创作了主题歌,还有大量晚会歌词,甚至出过近200首歌词的专辑《陈彦词作选》。
“写影视主题歌词,要把几十集剧本看完后提炼出主题来,挺麻烦的。但写歌词显著提升了作品‘魂灵’部分的概括能力,这对戏曲创作是很好的历练。一部2个多小时的戏曲作品,一般有300句左右的唱词量,而唱词是戏曲剧本的‘脸面’,得讲究。作品的深度、宽度、文学性都在里面。”陈彦说。

32岁那年,已是“获奖专业户”的他,遇上了新“烦恼”——院里面准备提拔一位年轻团长,正处职。
他在犹豫。在他看来,那是最好的创作年龄;约稿的机会很多,影视剧本、歌词等稿酬那时也十分可观;工作比较自由,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而且当时他认为“做团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主要怕耽误了创作。但领导还是希望他当,几个副院长也做工作,他就当了青年团团长。
这是一副很重的担子,为此他不得不推了很多活儿,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只写了一半就撂下了,从个人收入上讲应该说损失很大。“上百人的摊子,你一天不操心十个小时以上是干不好的。何况青年团是戏曲研究院的名团,得出人、出戏、多演出。”陈彦当了四年半的团长,又当了三年多管创作的副院长,再当了十年院长。这期间,他为单位义务创作了《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舞台剧代表作。
那十几年,他基本上是早晨六七点进单位,晚上演出结束到后台看看大家,与相关人员说说第二天的事再离开。精力投入很大,当然,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后来都作用于戏剧与小说创作了。
陈彦说:“其实创作与公职之间也不完全矛盾,如果我没有参与到一些具体的公职生涯里去,写作也许会缺少很多维度。我老对一些青年创作朋友讲,别太把创作搞成专职,那样路会越走越窄,该干嘛干嘛,永远抖动着那根创作的神经就行。任何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就像相机里的感光元件那样,作家要学会‘感光’——紧紧抓住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的那些特别场域的丰富体悟,成就你不同于他人的独到表达。作家需要孤独,但不可闭门孤守,不可圈子化,几个人老津津有味地说那点事儿,麻烦就大了,视野、思维窄化、固化、僵化而不自知。”
生活,是陈彦创作的另一大基石。

要兼顾管理与创作,陈彦有着自己的独门时间管理秘诀——不应酬。他说:“陕西人热情好客,一进酒场,没有三四个小时出不来。只要爱好这个,几乎天天都有‘场’,没有自己也可以约嘛!热情是热情了,‘好客’的圈子越来越大,耗的时间就越来越多。时间这东西,哪敢细算哪,三四个小时你想要干多少事?”
在西安的30年,陈彦的阅读习惯也在逐步“升级”。当副院长和院长的十三年,无论严寒酷暑,他总会一边晨练一边背书,日复一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十几年他坚持背诵了十几万字,是与古人心境在沟通,更是在补传统文化这一课。这是笨功夫,却也是最宝贵的硬功夫。

文学艺术应当给普通人希望,
首要目标是“真”
商品经济时代,很多人需要看得见的利益,但创作很难和利益直接挂钩,无法“刀下见菜”。因此,镇安昔日出现的青年作家群体中,很多人写着写着就转行了,陈彦成为坚持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这需要定力,需要坚持。
从写小说、散文,到编剧,再回归写小说,这是机缘、是爱好,更是一种坚持——写出时代的困顿、挫折与光亮,陈彦说:“我们得给人生煨起一堆向天的火焰。”作家应该给人以希望,尤其是要给普通人以温情、温暖与希望。如果世界没有希望,人还怎么活下去?“写作有千万种理由,这是我个人坚持写作的意义。”
陈彦认为,作品的“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真”剥离,那“善”也成了“伪善”、“美”也成了“伪美”。艺术之“真”,当是作家努力追求的境界,“说我擅长写小人物,也是因为熟悉他们,努力想去追求‘真’的层面。”
为了写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舞台剧《大树西迁》,陈彦在西安交大住了四个半月,又在上海住了35天。上海的夜无比迷人,他却爱上了外滩的“静”:从徐家汇步行到外滩,那时外滩还不像现在这么繁华,他静静地品味与思考,一边是历史,一边是即将拔地而起的未来。
其间,他采访录音搞了几十盘,还做了很多笔记,就是找不到下笔的感觉。到处都是宏大叙事。西迁本身也是宏大叙事。他绞尽脑汁,最后只能从一家四代的普通西迁教师入手,努力去折射那部史诗的宏阔意象,“我只触摸到了我所能认识到的那份‘真’”。

“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是一个世界性的文艺创作话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看,整个社会的基础建设,也是最普通的劳动者创造的。但他们的光和热被遮蔽太多,值得全社会去深切关注。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是一个打拼者、奋斗者,从中国最基层开始,和这些人物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对他们特别熟悉。”陈彦说。
曾经,陈彦办公室窗户下就是舞台的后台口,装台工的生活景象击中了陈彦的内心,同时他自己也经常参与装台、拆台。“但凡遇见紧急情况,或外出演出,我都参与过装台、拆台的活儿,集体干着有劲。演出完大家都很累,领导带点头,会让大家觉得大家庭挺温暖。”他与装台工混搭在一起过,写起来自然就得心应手许多。
刁顺子们都是非常丰富的生命个体,只有深入到内里,才能看到他们的生命肌理。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陈彦对每一道环节都细致入微。比如角色的名字,特别是那些有着鲜明特色的角色,“作家取名都是有想法的。比如刁顺子,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辩证的名字,他勤劳、善良、厚道,有时也有些狡黠,甚至‘鸡贼’,小人物得有他自己的生存智慧,有他的处世之道。”他说,“有时也会随便取些名字,比如小说里的周桂荣,就是为了写她极其普通和平凡,就把最平庸的名字给了她,为了表现她的大众性。”
而刁顺子女儿刁菊花,小说在塑造过程中,陈彦说他“下手较狠”,而电视剧做了“软化”处理,得适应大众审美心理,那是完全必要的。他之所以“狠”,是因为他觉得一些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受到了巨大挑战,甚至包括他们的儿女,已经从身到心,远离“既没本事也没钱、还靠肩扛背驮过活”的父母而去了。

写《喜剧》最快乐时,
摔在沙发上笑到泪水奔涌
镇安的25年,西安的30年,陈彦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陕西文化烙印。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体现就是陈彦作品中十分注重陕西方言的运用。“尽管方言写作会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但方言写起来确实很畅美。《水浒传》中,那些民间方言就很有意思,越揣摩越有味道。仔细分析会发现,方言表述会更准确,更有力量,也可能更有生命活性。”陈彦以陕西人邀请别人吃饭举例,普通话“咱们晚上一起聚一聚好吗?”,关中话就是“黑里咥走!”这种“洁快”瞬间就能体现出地域人物性情。
“我们现在都在用的语言,‘大路货’太多了。我喜欢用方言写作,这也应该是作家对地域文化保护的一种探索。当然不能过于生僻,得从字面上找到辨识度。”陈彦说。

2019年,陈彦离开居住半生的陕西,来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除了家人在身边,他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并不多,生活也更加简单,一年到头基本就是家里单位两点一线,再就是看戏,这是工作的一部分,现在疫情期间,戏也少了,其余绝少应酬。读书写作仍是他工作之余的常态。
陈彦的生活习惯多年来很少变化:喜欢在身边放些干果,写作时“当烟抽”,一天能吃三四把;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左右晨跑或夜跑,一小时跑六七公里;心乱之时铺开宣纸,练练书法,以临帖为主,能让自己静下来。
谈及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喜剧》,陈彦透露,是描写舞台上演小丑的父子三人,以及由他们散枝开叶所带出来的百十号人的演艺、生存故事。“《喜剧》和《装台》《主角》是相关联的写作,但都独立成篇,其内在算是舞台艺术创作的姊妹篇吧。”
相对于《装台》营生总系于一业、《主角》众生皆备于一人,《喜剧》则是苍生终执于一念。它把“角”和“台”置于“剧”,将剧场剧情剧中人放还于乡野,演出的是美丑悲喜对照转换的民间大戏,装载量更大。
由此,“舞台三部曲”长篇系列成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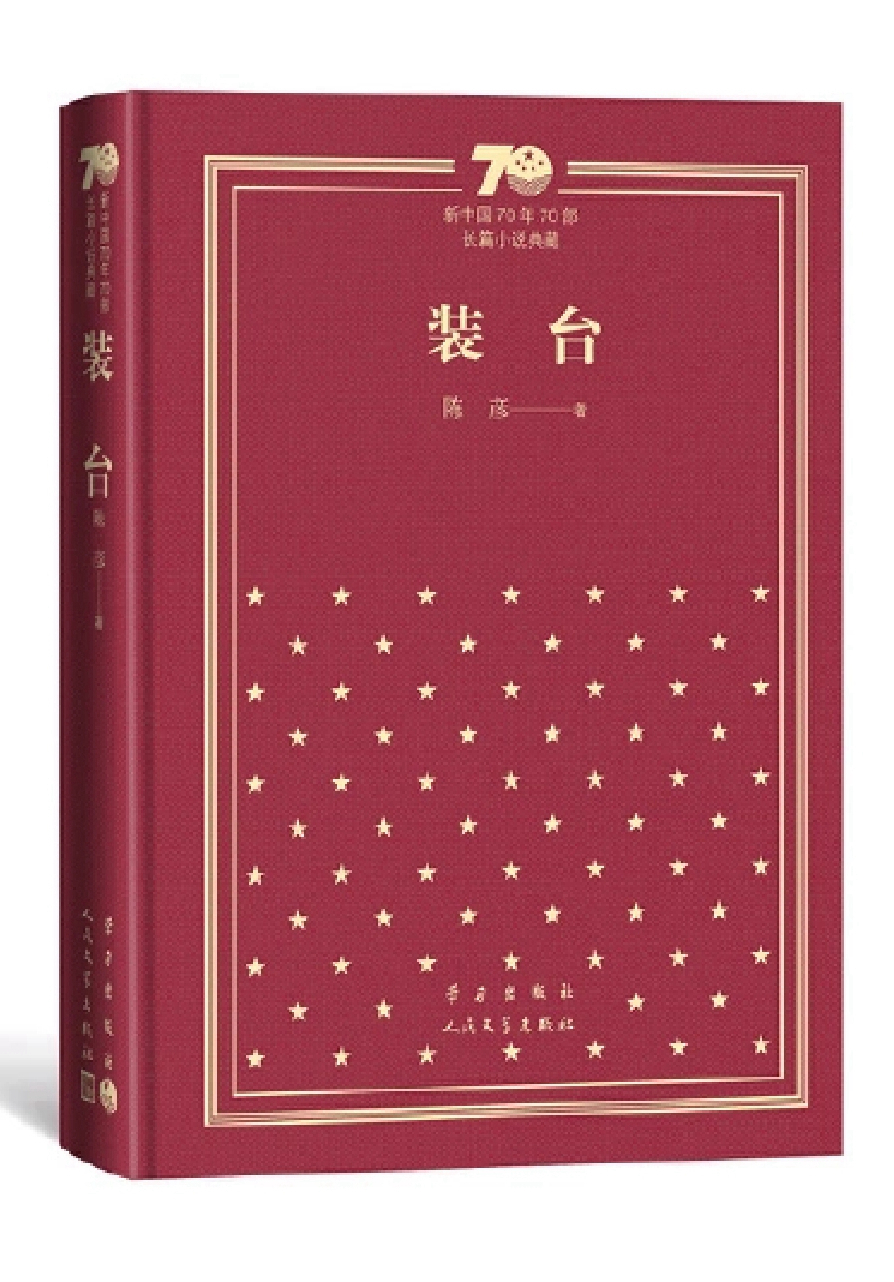


采访的最后,陈彦回顾了创作生涯最艰难和最快乐的时刻。“我写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相对艰难的是《大树西迁》。起初,让我创作这部剧的张迈曾先生,希望制作长篇电视剧。但我因为不熟悉,和自己的生活有距离,啃了上百万字资料,记了好几本笔记,最后只写了2万多字。”他说,“最快乐的时刻,常会有,比如写《喜剧》的过程中,有些地方笑到自己泪水奔涌,甚至站起来把自己摔到沙发上,纵情大笑。”
对于年轻作家,他也给予了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建议。“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具备真实的艺术异质创造、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张力这三大基础,当然,肯定是有思想要阐发。不想说个啥,你费那神讲那故事干啥?对于年轻作家而言,需要向两个方向去努力:阅读上开疆拓土,尽量朝宽泛的读;生活上细嚼慢咽,那就是琢磨好自己最熟悉的脚下的方寸之地。”
“技巧永远是第二位的。或许也有例外,有些人能通过想象力去弥补。但我不是。”陈彦说,“我就是一个特别依靠生活的作家,其实生活中间就充满了奇思妙想与意识恣肆汪洋无尽的谋篇布局与结构。”
作者: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记者 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付鑫鑫
图片来源:陈彦 魏锋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官网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