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纸关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报道
1964年10月15日,法国哲学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萨特从《费加罗文学报》上得知他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看到新闻的第二天,他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拒绝信,随后在《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但10月22日,评委会还是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给他,其理由是: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
根据创立者诺贝尔的个人遗嘱,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在信中写道: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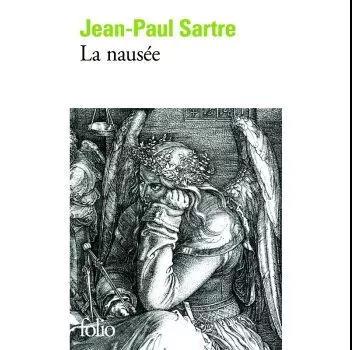
萨特获得诺奖的作品《恶心》(La Nausée,又译《呕吐》)
萨特是一位写出《存在与虚无》的存主义学者。而存在主义坚信人存在的意义是无法经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的,个人是独立自主的。萨特是因为他是萨特而存在,萨特拒绝用普世公认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证明萨特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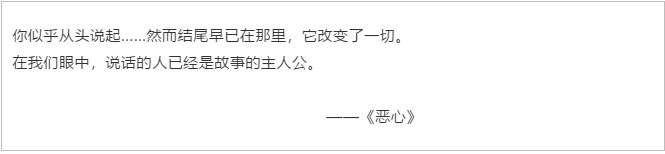
镜厅中的孩童
1906年9月17日一个叫让-巴蒂斯特·萨特的人长眠于法国西南部蒂维耶镇附近的小农场。他做了什么,值得人们如此注意呢?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职责——他作为一个丈夫的职责:1904年秋的一天,他使安妮-玛丽·萨特,这个他在五月迎娶的姑娘怀孕。
这个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取名让-保罗-夏尔-艾马尔·萨特的孩子,有朝一日将成为“萨特”,进而从遗忘中拯救其父亲,并赋以某种间接的不朽:儿子生下了父亲。但当半个世纪后,萨特试将自己的生涯形诸文字,提及父亲的仅寥寥数语:“直至今日,我仍为对他知之甚少而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爱过,想活下去过,也曾感觉到自己奄奄一息,这些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了。”我们决不能为这讣闻的简短所误导:。但当半个世纪后,萨特试将自己的生涯形诸文字,提及父亲的仅寥寥数语:“直至今日,我仍为对他知之甚少而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爱过,想活下去过,也曾感觉到自己奄奄一息,这些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了。”我们决不能为这讣闻的简短所误导:。

少年时的萨特
萨特随母亲回到外祖父的家中生活。比起写作,阅读在他的生命中到来得更早。通过自学,普鲁狼吞虎咽地阅读着外祖父藏书室中的一切。在一个19世纪的文坛成员的藏书室中能拥有的一切在这里都应有尽有,理所当然的,这小孩被灌输了半世纪前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中主导的文化和观念。我们并不是很确定普鲁是否真的很享受阅读拉伯雷、高乃依、拉辛、伏尔泰和维尼,但是在他几乎不能理解他们这一点上还是很清楚的: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理解高乃依关于荣誉的概念呢?当马车在鲁昂的街道上奔驰时,爱玛·包法利和莱昂正在车厢里干什么呢?在成人的持续凝视下,他模仿着读者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正在阅读的书的姿态,正如普鲁(萨特幼年的昵称)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孩子一样,他也是一个装腔作势的读者。
对他而言比较幸运的是,在公然地期待他变成一个书虫方面,他母亲和外祖母并没有外祖父那样热情。只要给他读一些更适合他年龄和理解力的读物就可以疗救他。一开始给他的是非常通俗的连环画漫画书,继而是少儿经典:儒勒·凡尔纳、《尼古拉斯·尼古尔贝》、《最后的莫希干人》。萨特把这些当作“真正的书”。非常有趣的是,在现实和想象之间那种强有力的对抗中,“现实”或者是“真实”与次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二流的文学(连环画、孩子们的书、侦探小说)、电影和未成年的他们自己联系在一起:他只能从边缘处孤独地看那些在卢森堡公园里玩游戏的孩子们。

年轻时的萨特
他的第一部“小说”叫作《寻蝶记》(“For a Butterfly”),它完全是从他读过的一本连环画书里抄来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幻觉从未被触动:“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绝不会成为作家了。”
这个孩子对写作的虚构其实是他虚构自我的方式:被成人那种篡改孩子、使孩子支离破碎的凝视目光扭曲和曲解的孩子怪物,现在可以开始变成一个简单的孩子了:“我在写作中诞生;在这之前只不过是影像、映像的游戏;从写第一部小说时起,我就知道了一个孩子已经悄悄滑入了镜厅之中。”
外祖父转移了普鲁的志向,朝着一个显然更高贵的目标:他该成为——如施魏策尔历代一样的——教师;教师可以附带地搞点写作。夏尔为普鲁预见了一个非常安静平庸的命运;个孩子却把它转换成了追寻文学不朽的梦。
被建构的绝对基础
直到在路易大帝中学的第二年萨特才发现了哲学的乐趣,而以前他把哲学视为一门相当枯燥的学科。因此作为一个学哲学的学生,萨特于1924年进入了巴黎高师。如此一来,他真正加入了知识精英的行列。那个时代在巴黎高师占统治地位的哲学风格是批判性的或者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的。
对于他而言,萨特显然停留在没有雄心成为一个原创哲学家的层面。在至少两个方面,萨特只是把哲学当成他生命的真正活动——写作的附属。首先,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不得不养活自己,而教授哲学是谋生的一种方式。其次,他视哲学研究为作家写作活动的补充:作家的工作是要揭示世界和人类境况的真理,而在哪里能比在哲学中更好地发现这些真理呢?但是大陆哲学的主要研究模式对此不是很合适。尤其特殊的是,他的实在主义也是对他自己的反抗——反对作家长期习惯性的唯心主义,即把词置于优于物的特权地位,也就是说重词轻物。只有当几年后他发现了现象学,他才能就敌对的唯心主义者和实在主义者趋向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萨特把他在巴黎高师度过的岁月描述为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们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正是在巴黎高师,他开始塑造自己为他人眼中的不朽人物:他是如饥似渴的读者,不知疲倦的作家,他似乎拥有无尽的从事艰难工作的能力;但是他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变成了宫廷小丑,但是任何惹了他的人就麻烦了:他的讽刺挖苦、机智狡猾和语言暴力都是出了名的令人恐惧。他把自己变成了那个曾经非常纤弱又被过度宠爱的小男孩的绝对对立面,当其他的男孩子们在卢森堡公园打作一团时,那个小男孩只能再一遍瑟瑟发抖。

萨特和西蒙·波娃在巴尔扎克纪念碑
萨特真实的生活和《恶心》主角罗冈丹虚构的生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他在《词语》中写下“我就是罗冈丹,我非常冷静地通过他表现我生活的全部质地”时,他毫无疑问就是想要效法福楼拜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Mme Bovary, c’est moi),当然现在看来这仍是一个成问题的口号。对此,萨特似乎已经非常慎重地增加了他与他的人物的不同,但是这些差异全部是表面的,它们所揭示的他们生活的“质地”恐怕是相同的。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就他们创作文本的方式而言,还是就他们与写作活动的关系方式而言,我们都必须看到他们身份的本质和限度。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作家。罗冈丹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一个“业余作家。罗尔邦传记的书写并不是必然性驱使的,没有迹象表明写作曾经在罗冈丹以前的存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萨特则相反,他活着是为了写作:写作从童年起,就是他生命中根本性的活动。“根本性的”这个单词的强烈意义是:写作是他的生活被建构起来的绝对基础,其他任何事情都从属于它。
战争和人
关于战争年代对个人的重大意义,1975年萨特毫不犹豫地说:“我生命中最清楚的事情是我曾经有过断裂,这意味着两个差不多完全分裂的时刻……战争前和战争后。”经历了“二战”的人大多都可以理解“二战”作为一个断裂把他们的生活分成了一个“之前”和一个“之后”,但是萨特这段话要表明的是,这种断裂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后来的萨特几乎不能识别以前的自己。
客观地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残酷的变化了:他从世界的文化之都,突然被运送到一系列寂静的阿尔萨斯村庄。在巴黎,钦佩他的女性朋友和情人的小圈子一直围绕着他,现在他发现自己身处最富侵略性的男人的环境。实际上,直到那时,萨特一直过着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精英圈子的生活。现在,他只是萨特,一名隶属于气象陆战队的二等步兵。他发现自己被迫与来自非常不同社会背景和眼界的人共处:法国电话公司的职员、从事服装业的巴黎犹太人、外省老师。

1960年,格瓦拉(右)在古巴会见萨特(中)和西蒙·波娃(左)
他读“一战”的历史,读纳粹兴起的分析,似乎尝试最终理解他是怎样来到他所在的地方。他阅读哲学和传记(他长期着迷的事情之一)。他阅读历史和小说。他常常一天一读就是12个小时,直到他那只好的眼睛“眼冒金星”(自四岁以来,儿童时代的疾病已经使萨特实际上右眼失明了)。他同时也写作。反思萨特在假战争的九个月中所写的这些巨量的文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真相:他是一台文本制作机器。
他写作了并且重写了将在 1945 年出版的那本厚厚的小说《不惑之年》的草稿。尤其是他生产了一本战争日记;1995 年扩充版的这部日记有 600 页之长——它只包含了在这一小段表面上“无为”的时间里他完成的 15 本笔记本中的6 本!可能除了 1958—1959 年当萨特写作《辩证理性批判》时使用苯丙胺兴奋剂而过度活跃之外,这九个月肯定是萨特整个生命中最密集的文学创作时期。他写作,似乎他的生命都依从于写作,而且在很多方面,的确如此。

1950年,萨特和西蒙·波娃在北京
他经常重复申明战争已经“改变了”他,申明同伴之谊、被囚禁和被占领的经历已经把他从一个冷淡的个人主义者“转换成了”激进主义积极分子,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日记的死后出版,这个申明也可能已经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了。但是日记的意义正在于它使我们能够目击改变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使我们问我们自己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使我们反思在这个自我转变过程中写作所扮演的角色:日记既是一种转变的记录,同时又是转变得以发生的必然方式。如果有人仔细核查在这段时间里写作对于萨特而言所扮演的各种功能的话,他将深入到艺术家与其媒介关系的核心。
像大多数应征入伍的士兵一样,萨特对处境的第一反应是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迷失感和自主权的丧失感。然后,不出意料的是,写作的日常实践的第一个功能就在于帮助作家重获他的位置感,或者“重新定位”他自己并且再度确定他虚幻的独立性。在“外在”(他人、死亡的可能性、军队的等级制、敌人的意图)非常重要并且威胁要压倒或者侵入“内在”时,写作是一种重新确定内在性特权的方式。

1939年到1945年间一个客观改变仍然发生了:那个“金权民主主义(plutodemocracies)的抽象的人”变成了一个具有社会承担的知识分子。再一次强调贯穿在《日记》中的各种线头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个变革的主题通过对一个特定哲学概念延伸的反思而完成。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哲学概念是真实性但是萨特总是更擅长揭示不真实而不是自己去定义真实。在短篇小说《墙》中,萨特就已经在处理真实性概念与死亡的关系了。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相反——海德格尔提出死亡是我们“自身最大的可能性”——萨特已经在那篇小说中暗示出,死亡远非我们的生存被不停地导向的那个顶点,死亡不过是荒诞性闯入了一个生命的核心:它并非一个协奏曲的最后那个决定了之前一切的音符,而更像是正在那个钢琴家头顶坍塌的屋顶:一个人总是死得太早,或者太晚,但是从来没有死得“准时”的。
萨特确信这种决定不可能是反思的结果,而肯定是在一种整个人格猛烈变革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这些就是《日记》中形塑他的思想的备选方案:反思或者自然发生;自我重复或者激进转变。

《萨特》作者:安德鲁·利克
来源:北大出版社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