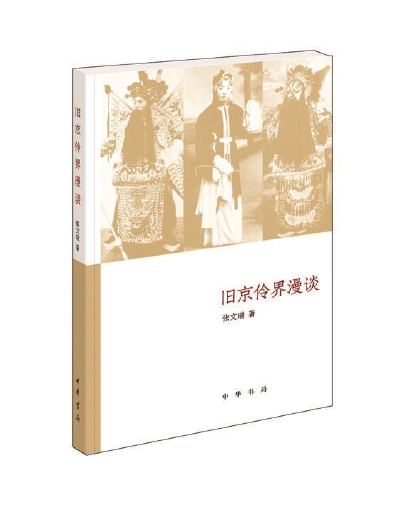
《旧京伶界漫谈》张文瑞著中华书局出版
旧京民俗文化丰富而广博,韵味无穷的京剧文化正是其中尤其灿烂的一笔。本书通过大量切实可信的资料,辅之以流畅的笔触,帮我们补上了旧京伶人的生活与艺术这有趣的一课。本书作者生于老北京家庭,其父是票友,宗余派老生,与梨园中人多有交往;几位兄长皆能拉能唱。作者本人数十年受此熏染,对京剧文化抱有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京剧类书籍。近20年来,侧重对京剧文化做了较深入研究,伏案三年写得此书。

谭鑫培便装照
台上台下机智过人,不惧刁难
谭鑫培20岁上下时在京东一带搭“粥班”(乡下戏班收入微薄,时常喝粥,故名)。一日在某村演完需赶包下一场,两地间隔数十里。此时太阳眼瞧落山,众人疲乏至极都不想再走。谭鑫培恐误场而影响戏班儿生计,遂对众人道:“前村不远就有客栈,我们不妨住一宿,明早赶路不迟。”大家满心欢喜进了村子。不料只是个小村庄,根本不见客栈。谭鑫培顺手指着一户院门对众人道:“就是这家店,我认识里面的少妇掌柜,咱们今夜宿此,当有佳趣。”众人欢喜,争相叩门。果然有位少妇秉烛而出,问几位敲门何事。谭鑫培答以借宿。少妇道:“我家无男人,不能留客。”谭闻言说:“正因为你家无男人,我们才要住在你家。”少妇一听怒极,大声疾呼有强盗,乡里四邻群起而至。谭鑫培慌忙对众人道:“不好,惹祸了,快跑!”言罢飞奔而出,其他人亦以极快速度紧随而逃。村民点燃火把,手持锄镐拼命追赶。戏班儿众人狂奔至天亮才摆脱村民,个个笑颜庆幸未遭暴打。谭鑫培道:“你们还说累吗?”至此大家才知被谭鑫培捉弄。又行数步,忽闻锣鼓声,再一看,下一场的戏棚就在眼前。
有一次老谭与金秀山唱《捉放曹》,大李五来吕伯奢。曹操上场本该唱江阳辙“秋风吹动桂花香”,陈宫接唱下句“行人路上马蹄忙”。金秀山上来后故意改辙,把“桂花香”唱成“桂花开”,老谭佯装不介意,随口改唱“弃官罢职随你来”。金秀山接唱“用手且把丝缰带”,老谭本想把“见一老丈坐道旁”改成“坐土台”即可。扮吕伯奢的大李五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闲得没事。他一瞧金秀山改辙开搅,也跟着起哄。本来他是“坐道旁”的,等老谭唱至“见一老丈”时,他忽然站起来了,而且示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之状。分秒之间,老谭唱出“在土台”三字。金秀山、大李五都没难住谭大王。
一次老谭在天津上天仙茶园应演。某伶是上天仙茶园的台柱子,妒忌老谭名气大又比不过,遂生邪念。他花重金买通老谭跟包,令跟包在老谭上场前使坏阴人。这天老谭的戏码儿是《文昭关》,伍员出台应该佩剑。迨老谭出台帘儿前,跟包将一把刀给老谭挂腰上了。此事瞬间被谭二发现,赶紧回身拿剑换老谭腰中之刀,可老谭已出场。谭二瞧着心急,台上有伍员手握剑柄及“腰悬三尺剑”的唱词。再看台上老谭,做表神态自若。起唱快板时,老谭临时改唱“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腰间空悬三尺刀,眼见仇人杀不了”,一气呵成,台下暴彩。上天仙某伶见阴人不成,反倒让老谭得彩,叹道:“小叫天之名是老天爷给的,人力不可毁啊。”遂向老谭再三认错谢罪,老谭一笑置之。回到寓所,老谭对谭二说:“今日之事总算侥幸,以后不可再有。”谭二转脸儿就把这跟包辞掉了。
幼年学戏耽误识字,晚年恶补
老谭打小学戏,十五六岁就搭班儿吃戏饭,自然误了识字念书。他会的戏大概比他识的字多。老谭平日在家于卧榻上翘着腿看报,一准儿是琢磨唱腔身段。别人只要见他拿报纸挡着脸,绝不上前打扰,因为都知道他报名也未准认得。老谭唱了一辈子《乌盆记》,当中“冒雨而归”也念了一辈子“胃雨而归”。别人顾及其名望,谁也不去纠正他。他晚年收了余叔岩,一天余叔岩奓着胆子对他说:“师傅,应该念冒雨而归吧,大概抄本上笔误了。”老谭听完瞪着眼道:“怎么?挑起老夫的眼了,你既有这样大的本领还向老夫请教干嘛?”吓得余叔岩非但没纠正得了老谭,连自己也老老实实念“胃雨而归”直到老谭辞世。
老谭早年在京师的身价不仅限于伶界,在政界他也有头有脸儿。不管那些王公大臣心里如何想,面儿上都把他当“贝勒”般捧着。老谭也十分拿得住劲,他与皇室宗亲尚书将军这类大官儿一起抽烟下馆子逛公园,都互称小名儿。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往下级别的官儿若能得“谭贝勒”颔首打个招呼,那是天大荣耀。一年某侍郎家娶媳妇,京官咸去贺喜。有人在侍郎府发现一精致雅间,外面候着两名下人。他扒窗一瞧,只见炕上摆着烟具,上首一客卧于锦褥,跷着腿正在吸鸦片。本家儿侍郎于下首打横儿坐着,轻声细语相陪。等缭绕烟雾缕缕散去,才看清翘足而卧者是谭鑫培。就听老谭说:“咱们是至交至好,你何必在这儿陪我,况且我躺这儿挺得劲儿,你不用担心,出去应酬客人吧。”侍郎这才起身出屋,吩咐下人好生伺候着。有翰林院徐侍读拜诣某显贵,逢显贵府上有客。只见客人独卧烟榻闭目狂吸“阿芙蓉”,一少年俊仆坐矮凳伺候烟灯烟枪。一会儿,客人起,与显贵耳语良久。因声音甚细,徐侍读只嫌耳朵太短一句也听不着,他暗忖似语涉宫廷之事。言罢,某显贵脸色如云雾顿开,打拱作感激状。徐侍读实在不解,无论如何想不出这位烟客是何方神仙,急忙跟下人打听,下人曰:“小叫天。”
老谭50多岁以后,眼瞧着晚生后辈伶人中时慧宝能书、汪笑侬能文、朱素云能画、刘永春能看相、贵俊卿会英文,各有应酬之技,唯独自己在王公亲贵前身份比他们高百倍,却写个名字亦需别人代笔,心中颇不服气。他花重金聘了位徐州秀才,应名管家会计,实则是教他念书认字。由《列国》《三国》《水浒》到笔记、子集一通儿恶补。若干年后,竟也添了几分书卷气,时不时还能掉几句文,只是常岔到两下里去。1915年,他由沪回京烟土被查没,提笔给他二姑爷王又宸写信告知此事,末了写“何物么,竟不容人理说。晚年遇此逆境,益复令人追想清廷”云云,也算难得。王又宸曾语人曰:“此老食古不化,然好掉弄文字。至其毕生,事无巨细惯走顺风,晚年值此,也怪可怜的。”
有一次老谭唱刘阿斗三字时,把“阿”唱作“挨”音,就听楼座儿一声倒好响起。老谭赶紧一瞧,盯准了这人模样,进后台就吩咐跟包请此人至酒楼小坐。会面后,老谭先恭敬三杯,然后言道:“适才唱得不好,有辱清听。不对的地方还请先生赐教。”该人也是不客气,答道:“您蜚声京城内外久矣,算得名家,可字音怎不能辨正?”老谭道:“愿闻其详。”该人曰:“阿字于蜀地念厄。”未及他说完,老谭当即跃起击掌嗟叹:“然哉然哉,刘备主蜀国岂不该用蜀音。”言罢下座三揖以谢。
行走江湖谨慎自律,为人仗义
辛亥年清室逊位,老谭一时颇念旧主,在京有段时间未露演。他的管箱跟包嗜赌,竟偷偷把老谭的行头送进当铺换钱还了赌债。不久沪上新新舞台邀老谭南下,启程前一日,管箱跟包仍没钱将行头赎出。他怕到了沪上临时没行头,那娄子就更大了,赶紧把实情告与老谭,且认错追悔。老谭听完大怒,立时就想把他打发了。可念及他跟了20来年还算忠诚勤恳,遂对他道:“幸亏衣箱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不过几件旧蟒靠而已。若是上等行头,一时我也没许多现钱去赎,那就误事了。给你50块,赶紧把行头赎出来,到了沪上再从你份儿里扣除。下次再敢私自动一件,趁早儿去别处吃饭。”管箱跟包感激万分,发誓终生报效老谭恩情。到了上海,这跟包伺候得极其细致,竟致劳累生病。老谭把他该得的戏份儿一分没扣,全给了他。
光绪庚子年(1900)后老谭第三次赴沪回京途中转至汉口,回黄州祭奠祖坟。闻得乡邻陆某被逼无奈要寻短见,老谭询问得知:陆某一家老小有薄田数亩赖作糊口之资,十年前急需用钱就把这几亩薄田典给了同村富家。当时言明陆某继续种地,每年交些租子当做所用银钱利息,十年为期,到期陆某拿钱赎回田地。富家地与陆某地毗邻,遂起占有陆某田之心。每到秋收,富家既不向陆某收租子,也从不催要本钱。陆某以为富家念他所收不多无力交租,就得过且过没当回事。十年期满,富家要陆某连本带租一并还清,不然就把田亩过户。陆某再三央告,富家不允并告到县衙。县衙断令陆某限期交足本利,过期不交即将田产过户富家。
老谭听完,拿出200两银子,让陆某还富家本金及一半利息,并嘱陆某告富家:“你等为富不仁,十年不问息租,明显居有谋占田亩之心。你若想要全利,谭某必亲至州府大堂与你理说,到时候你非但利息全无,本金亦恐难保。”陆某叩谢老谭后,即刻前往富家学舌老谭原话。富家一听京城“小叫天”来了,竟一句不敢言语,收钱还地作罢。
老谭这次赴汉是由沪乘江轮而上,行至十二圩时,谭妻侯氏及儿子都到船舷甲板观看江景,只老谭一人独卧舱里吸烟养神。就在老谭似睡非睡的当儿,忽觉眼前有人影一闪,急忙睁眼一瞧,见半个背影似散舱客人。老谭赶紧起身查看,桌上一翡翠扳指不翼而飞,遂尾随追踪而去。至船顶无人处,老谭对这贼道:“四海之内皆是朋友,你缺钱花尽可跟我商借,何必偷我心爱之物。我是老江湖,你这两下子我岂会不知?今天你把扳指还我,我非但不把你送官,还另有薄酬与你。”言罢拿出两块大洋递到飞贼手中。贼人愧色无一语,掏出扳指交给老谭,不受洋钱而去。
迨侯氏和儿子回舱,老谭闭口不言此事。船过九江,老谭确定贼人已下船才告知老婆孩子。侯氏责他为何不交船方办理,老谭道:“出门在外以方便为本,何必多事使人难堪。虽说贼人可恶,你旅客也有大意之处,若自己管好行李,此辈断难下手。”转脸又对儿子说:“你们行走江湖定要谨慎,不可贸然揭人家隐私。”
作者:张文瑞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