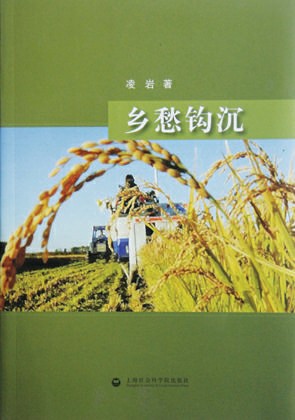
《乡愁钩沉》
凌岩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邓伟志
我与凌岩兄交往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我称呼他是我农业、农村、农民、农经“三农加一农”问题的顾问和老师。他不承认。几十年来,我碰到“四农”方面的问题,自己拿不准时就向他请教。他不是顾问胜似顾问,不是老师胜似老师。我知道他笔头很勤,是一位闲不住的秀才,可是近两年与他相关的研讨会上却很少能见到他。一打听,原来他在“钩沉”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历史故事。这几天我手不释卷地拜读了他这本《乡愁钩沉》书稿,方才明白他少开点会是值得的。
《乡愁钩沉》记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农村的一些片段,是作者从当年的工作笔记本上整理出来的,并且整理得那么详细、那么有趣。这些片段,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有印象,但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有些还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是不便张扬和传播的,因而虽不能说是“绝唱”,但也确实难能可贵。
比如,1981年安徽农村出现了万元户,上海“农经圈子”的同志多次开会议论:上海有没有万元户?直到1983年,终于“寻觅”到了两个万元户。这两个万元户所从事的行当可能有些离奇,一户是出租父亲单位关闭时分到的一些毛竹,给农民造新房的工程队用;另一户是专门从事培育水杉等树苗的。这都是合法而合理的,令人心悦诚服。
又如奉贤盐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已因海水趋淡而晒不出盐,盐民收入每况愈下。后来大家冲破计划配额,改养对虾,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全场社员普遍成了万元户,这种群体性富裕起来的景象,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我知道,凌岩兄曾当过十多年记者,擅长调查研究和采访,在县、乡、村干部中结交了一些朋友。正是这些朋友,给他讲了许多故事,掏出了不少心里话,或是抽泣含泪吐露的一些苦衷,或是只漏半句话的难言之隐,在当时是“不得外传”的,他只能写点“内参”,如今终于“解密”。
有一些是课题组的研究活动。当时“农经圈子”的同志对一些专门问题有争论,一时理不出头绪,搁置下来。现在情况透明了,原理清晰了,所以读起来既有情节,又有意蕴,成了有情趣的故事。有的是趣闻轶事,或是沉重的话题,现已时过境迁,但读起来却既有回味,又有新意。
《乡愁钩沉》所披露的,实质上多是当时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譬如公社(乡)要办商业,被说成“抢供销社的饭碗”;后季稻“看电影”(插秧过晚,灌浆不足,成熟期不垂穗),却不怪双季稻面积过大,而追究社队工业办得太多;社队工业稍有发展,就被说成是“利润转移”。
还如“贝可佩”在上海为什么“流产”?“灯下黑”是怎么回事?等等。
这里钩沉的一些碎片,为供人可读和引起兴趣,作者都提供了丰富的资讯、材料和情节,甚至还有一些知识性的论证,那当然都是常识性的。业内的常识对我这样业外的人来讲就是学识,这也足可以飨读者。例如:上海到底有多少个小城镇?在无霜期不很长的上海,是怎样设计推行双季稻的?盐场是怎样制盐的?几个农村铜管乐手是怎样用芦竹根段研制成与国际品牌齐名的铜管乐器哨片,并且引起巴黎哨片公司重视,成为出口热销产品的?泔脚(现称城市餐桌垃圾)曾对上海的养猪业作出贡献,并获得全国许多城市的效仿,但后来中断了。如今已在好几个城市被企业家开发为再生能源和有机肥料,等等。
林林总总,都是上海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背景、序曲和浪花,也是一些生动而形象的瞬间,是上海农经史的拾遗、捡漏和补缺。随着光阴的推移,时代的前进,知道这些的人将越来越少。如同许多新上海人只知道过黄浦江有七座大桥和十多条轨交、隧道,殊不知仅仅二十年前,还是要靠十多个市轮渡码头过江,除此没有他途。欲了解市轮渡是怎么回事,还得到档案馆去翻阅资料。然而这本书上的一些故事,即使到档案馆也是找不到踪迹的,故而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