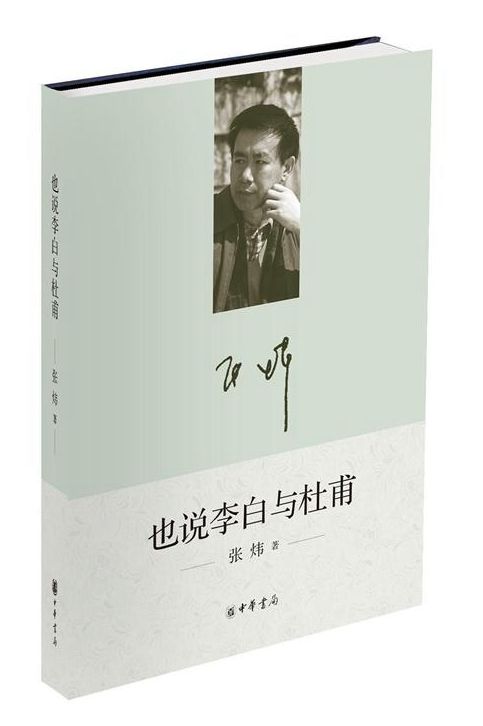
《也说李白与杜甫》 张炜 著 中华书局出版
李白和杜甫是两个天才诗人,让人敬仰和热爱。他们既是家珍也是瑰宝,是筑成一个民族诗性记忆的坐标,无论在民间还是庙堂,都早已演变成了一种符号。自唐至今,对李杜的评说从未停止,研究者不乏大家高手。言人之未言都是问题,何谈新意、创见?张炜是个执拗的人,他的执拗来自他对真理的痴迷,《也说李白与杜甫》即是明证。
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一个大文学家对李白杜甫的诗性概括,侧重点在李杜的诗艺,这也是多数研究者的路数。之前某些李杜诗艺解读常见的局囿是:过于强调指向和归宗,对艺术和人性分析粗疏和浮露,缺少温度,没有激情,跟诗的酿制基本不搭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评说,不同程度地过于偏执社会学分析,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偏离研究的方向,我们看到的李杜只是一个侧面或一个幻影。《也说李白与杜甫》洞开一扇大门,让我们放眼真实并纵身其中。
这是一部机智而有趣、诗意充沛的诗学著作,张炜以一个作家的情怀和忧思,以时代的深度和超前眼光,提出了崭新的创建。对李白嗜酒、炼丹、访仙、“浪漫主义”、杜甫“诗史”等问题都提出了新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天空降临”的李白和“自地面攀登”的杜甫;对李白的“走神”、“杰作与神品”等诸多学术问题,提出了卓尔不群的洞见,把文学赏读、文学批评、诗学研究、写作学及探究诸问题打通,并揉为一体,再结合当下网络时代文化消费之怪象,发出了自己清晰而强有力的声音。
以一个作家的眼光看李杜,当有不同于学人的发现。看李白的“仙气”不难,难的是看他的“人气”,那些沉默在角落的隐秘被张炜一一打捞。过去看李白炼丹,多以迷信论之。李白与哈姆莱特都有个难题,那就是生存还是毁灭(或译活着还是死去)。李白想成为超人,向往永恒,这显然是一切生命的“通病”和局限,是每个生命体至今都万难破解的谜题。但张炜把李白炼丹看作是对灵魂永生的追求,这是人生的大目标、大思维,即“终极关怀”,且与科学并不相悖。
习惯上对李白与杜甫的理解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说。这是怎样的误读?张炜对李白的“浪漫”并不否认,但对杜甫的“现实”就很是怀疑。杜甫不仅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漫卷诗书喜与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更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一向被认为低调之人,怎会酒后这样自吹自擂?“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张炜对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命题多有质疑:艺术创作也许没有什么“现实主义”,所有的创作都有强烈的浪漫性格。为了区分两种创作类型,可以临时贴标签命名,但给两个大诗人如此定性,就显出这两个概念的极大局限了。
对李杜诗的分析和研究是《也说李白与杜甫》的重心。这种分析和研究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李杜,寻找其本来面目。寻找之难可以想象,毕竟时间逾千年,其生命迹象多淡逝于历史烟尘;这种寻找又是痛苦的,因为寻找到的并非我们愿意接受的,两个光耀千秋、“旷百世而一遇”的伟大诗人怎么会有《与韩荆州书》《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样的文字?怎会利用盛名为一些富商豪吏写墓志铭?怎能做出让人脸红的“干谒”?这是我们不愿触碰的痛点,这会“令我们忍不住合篇而思,良久不语”。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李杜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谅解他们并能感受他们的无奈和痛。这种痛是深重持久的,因为这是人性之痛,文化之痛。
张炜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既在很大程度上宽宥李杜的“干谒”,又对造成这种令人痛心和不堪的文化背景给予深刻的批判:“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不过是‘主子’和‘奴隶’的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李白和杜甫的认识——无论是宽容还是苛刻,都会不由自主地从这种顽固的文化劣根上出发和生长。”文化最直接的产物就是价值观,这不仅影响社会的发展走向,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命运。张炜说:“国人的价值观十分简单和粗陋,许多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做官,其他竟然可以一概忽略不计。”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和价值观下的李杜,除了“干谒”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这样的价值观在今天又有了变种,官钱互喻,一个官场、一个“民间”,其意义是差不多的。
《也说李白与杜甫》循着两个伟人的思想脉络、情感里程,绘制了一幅意趣横生、文思丰盈的人物图。没有线性、平面,只有望不尽的遥远和看不到顶端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