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者,境界、处境、境况也,在这个可大可小的名词前再加上“一切”这个代词,其所指也就大了去了。庆山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以《一切境》这三字命名,内容之宽可想而知。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在《一切境》中,记录了写作和出版《夏摩山谷》后的这几年生活。独自在家静闭,令人思考更多。对自身也有全方位的整体性回顾与检查”。这就意味着《一切境》所涉时间大体在三年左右,至于空间,既是“思考更多”,又是“全方位”“整体性”,如此这般,以《一切境》命名也是实至名归的了。
无论如何,在中国文坛,庆山也罢、安妮宝贝也好,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客观存在:她的创作1998年始于网络却又很快远离,始终以一位个体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旅行、思考与写作;自打2000年元月出版首部小说集《告别薇安》后,迄今已公开出版作品20余部,尽管出版时间不是完全均衡,但平均下来就是差不多每年一部新作,大体是小说与散文创作交替进行;作品之题材不能谓之为宽,但所涉话题却不能称其为窄,尤其是散文创作更是天马行空;为人安静低调、为文唯美典雅,每一部新作的面世总会激起不小涟漪,虽未必算得上“爆款”,但绝对又是少有的每部作品都能持续畅销的作家……正是这一连串特立独行的“顽强”存在,想无视她都难,包括这部《一切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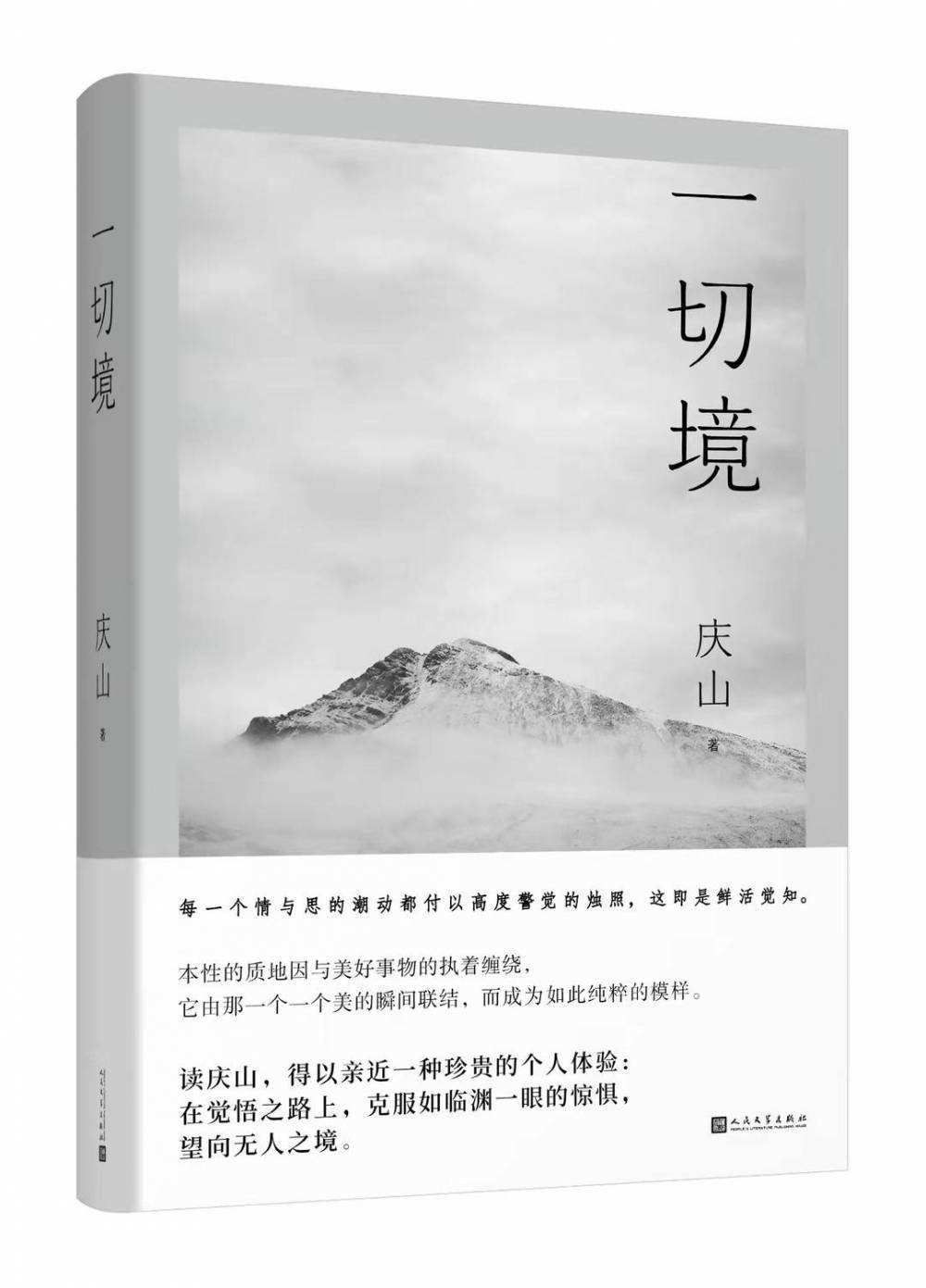
如果说庆山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尽管每一部都有不同的艺术呈现,但总体上倒也还是有迹可寻。而她的散文创作,早期的还算中规中矩,一则一题;但自打2013年的散文集《眠空》问世之后,干脆连这样的基本规矩也不守了。全书只是切分成四个大的板块,各占据50页左右的篇幅,每个板块下再用若干星号分割,星号与星号间就是一段段文字,多的五六段,短的仅一段,每段文字长不过百余字,短的则甚至不足20字,一种典型的“絮语体”。这部《一切境》虽继续延续了这种“絮语体”,但至少外在自由与模糊的尺度则更大。如果说《眠空》中的四个板块分别以“电露泡影”“荷亭听雨”“心如秋月”和“人杳双忘”这样的表述为题,我们大体还能猜出其所属板块的内容主旨,那么到了《一切境》中,四个板块的命名就分别成了“当作一个幻术”“曙光微起,安静极了”“简单与纯度”和“佛前油灯”这类不无禅意和玄像的表述,也更无从猜测其所属板块的主体内容,最多只能断定其多半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意念而已。
这样一种自由无度放荡无羁的结构与文体必然带来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质疑:散文固然以“散”为其特征,但“散”成如此这般没规没矩没心没肺的,还是散文吗?乍一看,这似乎的确是个问题!只是转念再一想,又有谁规定散文创作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呢?好像也没见过这样的“立法”,更何况还有“文无定法”一说。如果阅读这样的文字给你带来的不是心烦神散,而是心旷神怡心有灵犀,那又何尝不是快事一桩?
据庆山自述:《一切镜》,外观固然是碎片化的,但“内在是一条延绵而持续的心流脉络,传递对我来说,极为真实的记忆、情绪、感情与观念”,“散文裸露自己,一览无余”。作者有如此夫子自道,再读其文,确也大抵吻合。
比如,说到阅读,《一切境》中有这样的文字:“循着日记中的信息,陆续买了梭罗、卢梭、蒲宁、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托尔斯泰的几本书。现在读,时间正好。如果二十几岁就读,有可能武功报废。”或许担心上述文字为人不解,作者紧接着特地补了另一小段:“就像学打拳,先什么理论都不知道,上手就打。打一阵之后,再仔细琢磨理论,心领神会,领悟极深。不让阅读成为认知上的障碍,以致影响出拳。”说实话,第一段与我个人的认知与经验并不吻合。我一直以为,大量经典只有学生时代(无论什么生)才有可能阅读,进入职场后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就要被职业牵着走,所谓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职业读什么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况且这也不仅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拜我前辈所赐。待看了庆山的第二段文字后我就理解了她的前一段言说,作为一位职业作家持这样的认知很正常也很正确。我与庆山的差异很难说孰对孰错,无非是各自所持立场不同所导致。而且我还可以很自信地说,自己的说法可能更主流更正统,庆山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还是勇于直抒胸臆,这就是她的率真与袒露,而且肯定凝聚着她自己的思考。
比如,说到道德,庆山认为“不是独占,而是不剥削他人。但在某些男女关系上,已无欢愉可言。彼此剥削金钱与肉体”;说到母爱,在庆山看来“真正的母爱都夹杂着疲惫、愧疚、悲伤、艰辛、愤怒、孤独感等各种情绪”;说到中年危机,庆山觉得“大概是发现自己与变化的社会价值观慢慢拉开距离”;说到神秘主义者,庆山则直言这“是深感人生与物质世界受限因此愿意去探索的人们”……《一切境》中这样极简的语言和直觉式的表达比比皆是,即是庆山对自己。过往生活的一次梳理,也是一路探索与成长轨迹的某种呈现,恰似将自我内心置于阳光下的一次巡游,关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多个维度。态度简明直接,深刻记忆和隐秘情感率性袒露,在看似随感式的三言两语中裹藏着智性的成分。《一切境》所触及的话题当然远不止于上述四例,但基本模样大抵如此,也是这部散文新作在内容上最为突出、最为显著的一个共同特征。
再比如,“故乡花园里茶花正在绽放。鲜红繁复的花瓣,一层一层铺垫。这样扎扎实实地开着,沉浸在露水中轻轻呼吸”,这是安妮宝贝“时代”在长篇小说《莲花》中对花的描写;“兰花是一种特别的花,山谷里野生的那种幽兰,根须粗长,有动人心魄的香气”,这是《一切境》中对兰花的介绍。同样写花,两相比较,前者文字显然更唯美,后者则要清简得多。这细小的差异或许也可从中窥探出庆山对小说与散文这两种文体语言所持的一种态度:后者她更是讲究快速直接,单纯率性,敞开心灵,与人共享。
结束本文之前,还想说几句虽与《一切境》基本不相关但与庆山多少又有一点点关系的题外话。她的文学创作自上世纪末的1998年以安妮宝贝之名从网络开始出道,对这段历史,她本人的态度同样率真:“我2000年就离开了网络。对网络文学不感兴趣,不关注,与其无关。”
的确,庆山在所谓“网络文学”的领地驻足时间很短,但时间短毕竟不等于不存在。如果“网络文学”此说成立(现在的客观事实是:无论是否认同,“网络文学”一说似已成定论且还有蔚为大观之势),那庆山的“安妮宝贝时代”客观上无论如何都当仁不让应是其鼻祖之一。
我当然高度认同庆山这样的看法,即“根本不存在所谓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概念。文学只有好的作品和差的作品的区分。”所谓网络不过只是一方平台、一类传播渠道而已,它绝不意味着出现于这方平台或这条渠道上的文学在标准上就可以另立门户。网络既不是文学的“飞地”更不是文学的“特区”。在文学的基本标准上虽肯定有执行的高下之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另设一套标准,更不是降低标准。我曾经设想:假如一开始允许在网络上流通的文学作品其水准大体上与当年安妮宝贝的艺术表现相差无已,那“网络文学”这个词儿还会出现吗?即使有这个词儿,也绝对不会肿胀到现在如此庞大的体量。文学就是文学,“只有好的作品和差的作品的区分”,依托于什么媒介承载与传播在理论上并不重要。
然而,这个理论上本不重要的问题现在竟然变得重要起来,甚至还要为之完善与重构评价体系。这倒的确成了一桩无法解释的咄咄怪事,也无怪乎那个简单率真的庆山要与之撇清关系了。
作者:潘凯雄
编辑:范昕
策划:邵岭
责任编辑:黄启哲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