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轻时的黄宗英有个雅号叫“甜姐儿”
我与宗英大姐相识于198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那天,我在京西宾馆正为上海作家代表办理报到登记手续,只见一位身材高挑、身穿棕色皮茄克、足蹬马靴、留着长波浪发型的女士款款朝我走来,等她走近我才认出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后来得知宗英大姐刚从央视的电视剧创作中心《小木屋》拍摄地赶来北京参加会议,这是她第二次入藏。
从影多年改行创作成为“双料明星”
我与宗英大姐的交往是她与冯亦代喜结良缘后的事了。她患有严重的头疼症,止疼的药物含有吗啡成分属内控药,在北京没医保的宗英大姐开不了名为“再普乐”的特效药,只要一犯病就向我讨“救兵”。而我接到“求救信”后即到华东医院搬“援兵”,然后速寄北京。她给我的20余封书信就是这么来的,在信中她还告诉了我她得此病的来龙去脉。
1959年初,黄宗英正在电影《聂耳》攝制组中饰演舞女冯凤,一天,电影局领导突然宣布把她从电影演员剧团调至电影文学创作所,专业写剧本。黄宗英听后大吃一惊,头即刻疼得如炸裂一般,由于过度焦虑,就此落下缠绕至今的病根。
其实,电影局对黄宗英的调动并非拍脑袋的决策,事先也摸过底。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黄宗英与电影明星们积极投入到由昆仑公司组织的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演出中的报幕词、串连词、集体朗诵词和谢幕词全出自黄宗英之手,因而她被剧团称为“一支笔”。1952年她还出版了散记、观感的书,这在当时的电影明星中是很稀罕的事。翌年,黄宗英被上海电影局选送中央电影局主办的电影剧本创作讲习班,期间,她完成了第一部剧本《平凡的事业》。
被调入创作所不到三年,我国开始在表演艺术上对有突出成就的电影演员实行明星制,同时还推出了在全国各大影院张挂电影明星个人照片的举措。从影多年的黄宗英因改行而与之失之交臂。数年前,我问及当年错失跻身电影明星之列的机缘有无遗憾?宗英大姐摇了摇头坦然回答道:“干啥都一样,现在这样不是挺好么。”我对她说:“如今你不仅有众多的影迷,还有很多喜爱你文章的读者,成了跨界的‘双料明星’了。”她听后笑得很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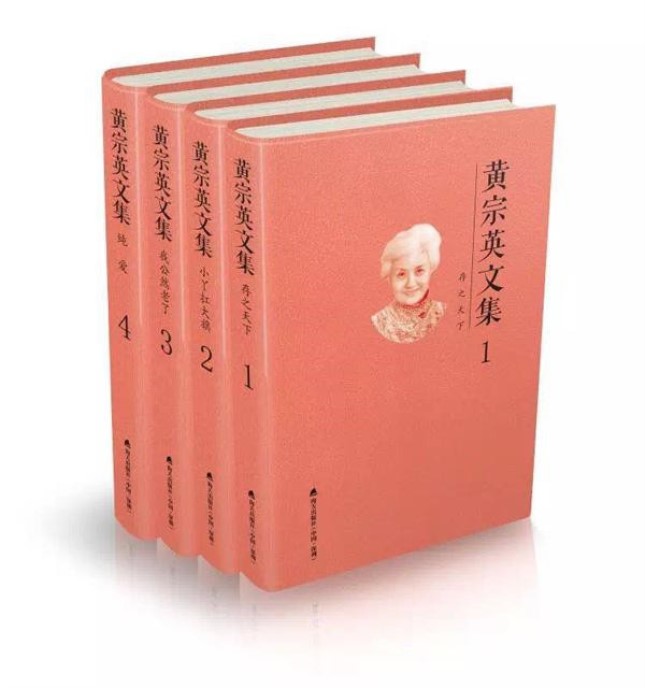
▲《黄宗英文集》共四卷:《存之天下》《小丫扛大旗》《我公然老了》《纯爱》
宗英大姐自脑梗后病情每况愈下,她的医疗关系在上海,北京的就医、住院成了最大的难题,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先回上海治病。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正伟,最好能为我约好21日入住华东医院郑安琳主任,加床也行……”2004年7月23日,我与同事李叶芳、冯沛龄到新客站接站,此次相见宗英大姐已无法迈腿走路只能坐轮椅车代步了。在去医院的路上,陪母亲来上海的小儿子赵劲得知我们在作协工作,便津津乐道地翻起他童年时的“老黄历”,从作协爱神花园里的普绪赫雕像和喷水池说到巴金、吴强、王西彦等老作家,就连老诗人闻捷同女作家戴厚英谈情说爱的情景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原来,这个小儿子是赵丹和黄宗英的最爱,当年时常被夫妇俩带着到处跑。此时,宗英大姐望着这个举手投足酷似赵丹的宝贝儿子,幸福地抿着嘴笑。
一段动人心魄的黄昏恋
我曾听说在黄宗英和冯亦代结婚的宴席上,老友们追问新郎和新娘恋爱的经过。“你们谁先开始说悄悄话的?”“听说你们写了100多封情书?”“不,是200多封……”“快老实交代!争取宽大!”朋友们围着黄宗英与冯亦代不依不饶地刨根寻底。黄宗英突然急中生智,说道:“我交代,明年,我们决定给你们看一个胖娃娃!”“什么?一个胖娃娃?”“是的。”黄宗英笑着说:“我们的胖娃娃,就是我和二哥的散文集《归隐书林》,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数年后,宗英大姐在给我的那本“胖娃娃”扉页上写道:“谢谢知音阿伟,藏此书多年矣,令我感动不已。黄宗英,2004年9月17日。”因未备名章和印泥,她用唇膏按其手指印替代了。
如果说《归隐书林》是黄宗英和冯亦代生的“胖娃娃”的话,那么,他俩300多封情书合编而成的《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一书,则是先结果后开花的又一个“小胖墩”了。那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情与爱,一段动人心魄的黄昏恋, 68岁和80岁两位老人鱼雁传情八个月,往来情书40余万字。宗英大姐使老夫子冯亦代焕发青春,而热情睿智的冯亦代也成了宗英大姐心灵的港湾。所以,无论是谁用何种眼光看待此事,宗英大姐都毫不在意。

▲《归隐书林》和《纯爱》见证了冯亦代和黄宗英之间动人心魄的黄昏恋
2001年3月19日,大姐在给我的信上写道:
阿伟:
……在有别人的帮忙下,历经毛四个月光景,已将手边所有冯致黄的情书199封(不含黄致冯的情书——本文作者注)输入电脑,并打印出来了,那是去年12月初吧,对健康的自我感觉很不好,觉得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免得自己倒下,别人很难有工夫插手,虽说情笺是准备谢世时发表的……
她把自己百年后出书的计划秘藏于心,连打印件也从不示人。一次,宗英大姐与忘年交李辉无意间说起此事,曾为黄宗英、冯亦代、赵丹编过书的李辉,感到把两地的情书合编成书信集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向她鼓动。宗英大姐经不住李辉的劝说,答应了。后来在李辉的介绍下,作家出版社很快与她签订了出版合同,而此书的责任编辑由李辉夫人应红担纲,起印三万册。
2005年8月,《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出版了。可是,就在出版数月前,宗英大姐心爱的冯二哥离开了人世,她怀着悲痛之情给冯亦代写了封天堂人间两相隔的“情书”作为《纯爱》序言。这篇题为“写给天上的二哥”的文章最后写道:“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愈加爱你的小妹。”
在宗英大姐送我的签名本中,唯独这本“情书”是没签名的,我也没有勉为其难。我至今保存着一大叠宗英大姐托我邮寄“情书”的名单,足有百十号人,还火急火燎地不时追加。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寄书名单给你后,还有十多廿来人未寄,帮我寄吧,说北京买不到,打电话来讨书的。”在她托我寄《纯爱》的一长串名单中,有季羡林、袁庚、徐凤翔、侯隽、舒乙、董秀玉、周明……
她把送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
宗英大姐送我的书上题得最多的字是“谢我知音”,有时也会让我惊喜一下,比如在赠我的电影版连环画《家》上题:“陆正伟好友,你是我的‘家’里人。龙年之秋于华东医院。”晚年,宗英大姐把送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她曾在北京返沪前夕给我的信中写道:“为自己的《上了年纪的禅思》以毛笔题词,签名,盖章156册(自己找累),累得像刚跑完5000米火炬跑,兴奋得停不住,我赶快去民航,挂内科急诊。”我心想,这是天生的性格,让她改也难。
数年前,新书一到,宗英大姐就托我把题签过的书成十上百地往外送,其中有《卖艺人家》《百衲衣》《七人集》《纯爱》等,用她的话来说:“钱从书里来,又到书中去。”出版社给的稿酬,还不够她送书的呢。我记得《七人集》出版后,作协给了宗英大姐100本,她像发牌似的很快送完了,又自掏腰包买了不少。就连陌生人讨书,她都会给。一次,宗英大姐转给我一个别人寄给她的信封,背面写道:“寄你此读者函,请你在《卖艺人家》书到后,将《纯爱》一并寄给盐场小学的老师。”

▲ 2002年本文作者看望黄宗英时为她拍摄的照片
宗英大姐在病房的小桌上完成了南通市赵丹纪念馆约她撰写的一篇自传,临近退休的主任医生郑安琳见了便想收藏这份手稿以作留念,但碍于情面没有开口。宗英大姐看出了他的心思,慷慨地将这份有着五六万字的手稿赠予了郑大夫。当我表示惋惜时,她只淡淡地说了句:“他喜欢,我就给他了。”
我有一位朋友平时爱淘各种老版本的旧书,他在上海书店偶然发现一本纸页泛黄的黄宗英早期作品《爱的故事》,便花0.15元买了下来,托我请宗英大姐在书上签个名。这天,我把那本旧书刚放到小桌上还未开口,她伸手已把书拿在手上了,神情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骨肉”,抱在怀里深怕再得而复失似的。随后她告诉我,这是她的处女作,家里原有的藏书经过几次动乱,已散失殆尽。
这本薄薄的书勾起了宗英大姐的回忆。1950年10月,黄宗英应邀出席在苏联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那年她才25岁,同行的有巴金、马寅初、金仲华、袁雪芬、刘良模。会议期间,他们到波兰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犹太人居民废墟以及工厂、古城。回国后,黄宗英陆续写了些见闻和观感,1952年结集出版了这本小书。宗英大姐提笔在书上为这位“有心人”写了封“感谢信”:“浦建明同志:谢谢你让我看到半个世纪前的自己,并初识了您这位知音,幸甚。黄宗英于上海华东医院,2006年11月24日,美国感恩节。”

▲2002年本文作者在黄宗英七重天居所为她拍摄的照片
我在与宗英大姐的交往中,发现她对身外之物看得格外淡薄,而乐善好施的情结又特别浓厚,只要听见有人遇到困难,她就会伸出援助之手。她一度把银行工资卡托我保管,每当我告诉她涨工资的消息时,她都会说:“又加工资了,老百姓要有意见啦。”我忙对她解释:“不单是给你们局级离休干部加,是普加,大家都有份。”她听后才不吱声。
2008年5月30日,宗英大姐给我来信说:“请在6月份为我取工资时,从我银行账号里取一万元,代我捐助汶川地震,汇费从工资中扣……”她虽长年住在医院里,但信息并不闭塞。一次,她不知从何渠道得知品学兼优的同济大学学生高河然患晚期急性淋巴白血病,生命已危在旦夕,立刻让作协的金嵩以“黄大姐”之名通过银行汇款捐助了一万元。
而今,20多年过去了,今年4月,我去看望这位已是九五之尊的老人时,她每天除了读书看报外,还手握软笔记日记呢。
我想,宗英大姐身上那股子浑然天成的天真,就是她无论在表演艺术上还是从事文学创作方面最为宝贵的本源。我祝愿她艺术之树常青,为读者创作出更多的名篇佳作。
作者:陆正伟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