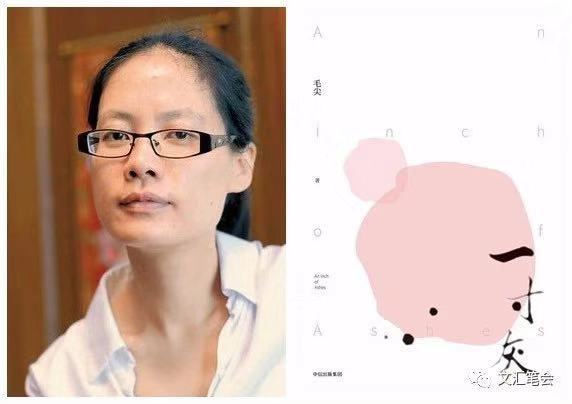
毛尖及其新作《一寸灰》
我写小说若引名言(famous quotes),则往往是为了捏造;写文章若引名言,就表示有“予何言哉”的慨叹。所以,在讨论毛尖的《一寸灰》之前,先把另外两个老姑娘的话张挂起来,完全是为了表示敬意。
“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话。
“世上最令人向往的,就是忠于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诚实。”这是苏珊·桑塔格的话。
在影视创作的小圈子里,人们勇于批判作品的时间不会拖得太长。犀利的实话伤人树敌,其影响何止吹皱一池春水,一旦投石击破水中天,读者也许有搔着痒处之快,创作者当其锋、受其凌割,即使脸上看似涟漪不兴,其实怀里风波迭荡。
然而江湖走老,胆子走小,山转路也转,人生毕竟不止如初见。我就认识好些个原本诚实犀利的批评家,一旦有机会,都争先恐后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干上了业者。我曾与友朋闲说此事,有位演员出身的导演答得轻巧,他说:“批评不是产业。”他的意思似乎是:到头来,人总是要往产业里奔的。
媒体的影评专栏当然算不得产业。不过,毛尖似乎从来没有放下屠刀的意思,算是个异数。每当我读她一篇评论文字,就很想“以环球为范围”地大声呼问:“还有谁没挨过毛尖一下子的?”
让我从反面说起吧。
若仍然以环球为范围,《一寸灰》里称道勉励的影剧作品也不多有。《刀背藏身》是其一。毛尖慧眼独具,点出“徐(皓峰)笔下的武林飘零人,常常并没有像样的生活,但最后,总能凭着中国人的朴素伦理,以侠士的方式至死一跃,虽然落花流水好像没有一点作为,但用他编剧的《一代宗师》台词来说,就是‘拼一口气,点一盏灯’”。甚至,毛尖还站在文学史的高角度上明快直陈:“而徐皓峰的武林,也至此告别了金庸梁羽生的壮阔江湖,那些为了余生不要鄙视自己、选择奋勇赴死的一介武人,成为当下中国人的对照镜。徐皓峰本人的文化抱负,亦显山露水。”
然而,即使在如此罕见的推奖之后,毛尖仍然要刀尖藏身,顺手捞起网上流传的“徐皓峰推荐的十二部电影片单”,下了手——“这个片单真心不错,唯一让我感觉有点遗憾的是,徐老师推荐了《教父2》而不是《教父1》,由此,回想我的徐皓峰阅读感受,我唯一的不满足于,好像跟对《教父2》的不满一样,感情生活多了点,这让他笔下的武林人物一上场就被一种脆弱感笼罩。”然后,这刀锋霍霍向“以环球为范围”的远方球场劈了过去:“这个,大约也是我看梅西特写时的感受。刀背藏身的武艺,跟梅西的球艺一样,太艺术了。”
太艺术也好,脆弱感也好,当然都和角色的感情生活有关。说得更简洁一些,《一寸灰》所反映的评家毛尖对于合格叙事作品的判准,大约就可以用夏目漱石当老师教英文的那个故事作为隐喻。他让学生翻译“I love you”,学生脱口而出:“我爱你。”夏目则说:“日本人怎么会这么不含蓄呢?翻译成‘今晚月色真美’就足够。”
我相信,这样的翻译一定可以立刻发展成无数夸张可笑的段子。不过,毛尖是认真的,她用“润物无声”来形容这个故事“传销了日本国家之美”的意义,“即便是轻小说,也常有一种天地万物不喧不哗的安静,生生死死都追求小津安二郎的态度,不失控不落泪。”
然而,这还只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现,无论视之为修辞之节制,或者是风格之简洁,都还是技术层面的事。毛尖在“不失控不落泪”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想法。
作为爱情的隐喻,无论是李商隐“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原文,或者看似粗拙实则另成颓废喻义的英译“one inch of love is one inch of ashes”似乎都有足堪玩味的“灭度”之义。
毛尖虽然不写小说不编故事,然而她直接承袭张爱玲(以环球为范围的话,就可以连简·奥斯汀也算上)的一点,就是将爱情这件事视为所有伧俗生活(比方说金钱)的象征,却正因爱情是一个象征,才得以摆脱那伧俗。于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才有可能说出那么迷人而准确的句子:“爱是种危险的劣势。”翻转成网络语言应该就是:“认真你就输了。”现实的你不得不认真,因为爱情所象征的种种现实都无比强大。
所以,毛尖关心的不只是爱情;讨论的也不只是电影。
我特别欣赏她在《柳暗花不明》里关于艾莉丝·孟若的分析。电影《你的样子》改编自孟若的《来自远山的熊》,媒体人云亦云,大肆数说孟若和契诃夫的渊源,然而毛尖独具只眼地谠论:《来自远山的熊》实则“完全是一个老年版的《仲夏夜之梦》”。不止此耳,她还犀利地说:“只不过,莎士比亚的喜剧故事,到了孟若笔下,染上了岁月沧桑,变成了时光蓝调。”没有刀光,仍可见犀利。
更多的时候,毛尖会拿作者“运用爱情”的手段和技法来评断其思想;这个角度往往锐利有效。她看《太平轮》,三句话道破吴宇森讨好观众的企图:“商业视角让他滑溜溜地两边讨好,他用爱情挽救国军,用人民赞美我军。”
然而毛尖并不以此为足,她更进一步拈出就在《太平轮》问世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派屈克·莫迪亚诺在一九七四年编剧、由路易·马卢执导的电影《拉孔布·吕西安》。作为对照,毛尖的攻略就不只是要修理吴宇森而已了。她是要借着上世纪七十年代行险而不求侥幸的两个法国创作者来提出一个天问:在战争(或者其他重大政治灾难)中,我们对于“不可能纯洁”的个人究竟是否有更富洞察力的宽容?而非借着市场倾心的爱情枝叶去掩饰空洞的情感。
无论模拟(mimesis)理论如何源远流长,论者甚至经常推源于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影子理论,从而进一步又推导出“再现”(representation)理论。然而,所有文字的、舞台的、影像的叙事,从不也总不与现实一致。有趣的是,评论家却可以有一个始终与现实颉颃上下的尺度去丈量作品意义和技巧的价值。
对于毛尖来说,即使现实中的歌哭血泪不时打动着凡夫俗子的日常与生命记忆,然而叙事作品的美学构成却必须包涵一种微妙的控制力,使“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必须受到驾驭。
更值得注意且不免会心一笑的,是毛尖并不会止步于“简练修辞”、“低度表演”、“朴素的场面调度”,她在《住到笠智众家》里,将小津安二郎沉静的、温暖的风格刻画成一种真实生命的情调。毛尖吆喝着奔赴那样一部她在年轻时瞠目以对的《晚春》,说得比文·温德斯更迷人:“笠智众(按:小津安二郎永远的男主角)以生活的名义收编我们,生活千手万手,他是观音;道路千条万条,他是罗马,他让我们明白,爱的最终魔法,是摒弃所有的手法和表演。这是小津电影的真谛,我也把它看成最高形式的爱。”
让毛尖说出这么激情的话,并不容易。然而,若非能够把自己的电影创作事业看成和豆腐工没有什么两样的小津,谁能经得起毛尖的诚实和犀利呢?毛尖不止一次在评论文字中暗示自己年纪不小,似乎意味着她的火气渐敛而返璞更殷,在我看来,《一寸灰》是《我们不懂电影》的一个强烈的补充。如果我们和毛尖一起调度起众多领域和面向的知识而更懂了一点电影(以及戏剧和文学),那是因为生命的现实也在催促着我们住进一个将雄辩都消磨殆尽的温暖小屋之中。我猜那情境恰是钱锺书先生所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会心人”所在。
作者:张大春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